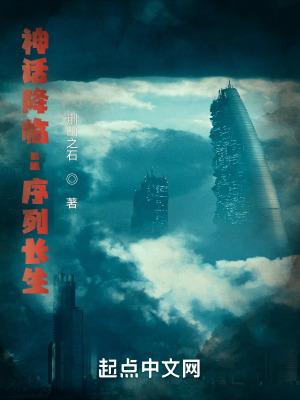笔趣小说>驭君 坠欢可拾 > 第56頁(第1页)
第56頁(第1页)
鄔瑾不也去裕花街看過戲,他也只是看了半天戲,怎麼都像是審問犯人一樣審問他?
對著少年老成的哥哥,他壯著膽子頂嘴:「你這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不等鄔瑾開口,他又道:「你不也去裕花街看過麻龍?怎麼你能去我就不能去?」
他把腦袋扭向鄔母:「就因為哥哥結交的是有權有勢的人,所以什麼都能做,劉博文是個商戶,所以你們瞧不起他!」
「偏心!」他猛地一跺腳,覺得很委屈,「偏心眼!」
他含著一泡眼淚,拔腿就跑,鄔母沉著臉,去牆角拿了燒火棍,提腳就追了出去。
鄔瑾添了根柴火,沒有出去勸阻鄔母,只在鋪子裡幫忙,等到天色濃黑,才背著鄔父回家去。
「哥……」鄔意挨了一頓胖揍,此時還在廊下罰跪,弱弱叫喚一聲。
鄔瑾先將鄔父送回屋中,又打來水,給父親擦身換衣裳,又送父親去解手,等安置妥當,才走入院子裡。
他伸手摸摸鄔意的腦袋:「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說罷,他不再理會鄔意,徑直回了屋中。
添油點燈,以杆撐窗,他身軀沉重地坐進椅子裡,呆看窗外夜色。
外頭樹影搖搖擺擺,零碎雜亂,野貓身手伶俐,趁著黑暗飛檐走壁,老鼠在陰溝里發出窸窸窣窣的聲音,野狗也在外低吠,吵鬧而又寂靜。
鄔瑾就這麼呆坐了一刻鐘,方才起身磨墨。
「元章二十二年,五初一,城外跑馬,遇石家兄妹,應是程廷作怪,與莫聆風賽馬,離馬場太遠,碰到了生羌,有驚無險,
生羌入寬州,必定生事,只盼能如趙先生所言,消弭此禍。」
筆下停頓片刻,又流連於紙上。
「殘花斑斑,金光重重。烏髮掩、珠潤色濃。風停草立,倚背生香。切莫縱馬,莫涉水,莫聆風。」
與此同時,莫千瀾走到長歲居,剛到院門口,就讓奶嬤嬤攔住了。
奶嬤嬤行了萬福禮,起身後,立刻用自己日漸發福的身軀攔在了莫千瀾面前。
「大爺,姑娘說不許您進去。」
莫千瀾本是占理的一方,然而因為處於下風,有理也成了沒理,故而訕訕地道:「睡了?」
「沒有,」不給他好臉色看,「在隔間裡。」
「我在外面看看。」
他做賊似地走了進去,踏上石階,躡手躡腳站到窗邊,腳不動,只伸頭,悄然打量隔間內情形。
隔間裡燈火通明,他那膽大包天的妹妹,穿一身雪白中衣和膝褲,褲腿和袖子挽起老高,跪坐在榻上,腳邊丟著一把團扇,身前放著一隻黑漆小几,小几上擺著一盞冰荔枝水,一隻白瓷碟子,裡面堆著切好的蜜棗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