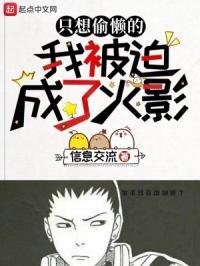笔趣小说>大佬穿进虐文后七千折戏 > 第八十四章 幕后祸首(第1页)
第八十四章 幕后祸首(第1页)
元隽这么一说,裴筠筠顷刻恍然。
“我就说嘛,”她轻笑道:“铁壁反叛的贵族,要刺杀,不冲铁壁侯去,反倒冲着你来,要不是蠢笨至极之辈,那就是好没道理之事了。”
她说着,淡淡一叹:“唉,这会儿真相大白了。”
“哪就真相大白了。”比起她来,元隽素来谨慎的多,不肯把话说死:“我已让叶檄去查了,真相如何,不日自会有定论。倒是你那头——”
他问:“袅袅的药何时能送来?”
裴筠筠没答他的话,只道:“放心吧,姜彦缨总算于你有恩,我不会让他死的。”
元隽一笑,便不问了。
没过几日,袅袅亲自从羽雁送药过来,知道医的是姜彦缨,还有些意外。
“铁壁暴乱刚刚平定没几天,城内城外正是人人自危之际,王爷连自己险些遇刺的事情都着令力压,更不要提救驾之人的身份了。”
给姜彦缨施针喂药之后,裴筠筠净了手从屋室中出来,同袅袅一路往外走,一路说着话。
袅袅闻言缓缓颔首,过了片刻,又问:“外头人不知内情,可铁壁侯府却一清二楚呀,怎么今日姐姐为他解毒,场面上却如此冷清?好歹是东宫近臣,不至于这么没人缘儿罢?”
“是你赶得时候巧,”裴筠筠停下脚步,朝府衙方向抬了抬下巴,“今日王爷临堂,主审当日行刺之人。”
袅袅观察着她的神色,想了想,问道:“那人有什么来头
么?”
她嗤笑一声:“可不正是有大来头。”
刺杀之事发生那日,元隽一见翟温,还只知他曾出现在冯通府上,直至昨日叶檄将手下调查所得呈上来时,这背后的水有多深,方才稍显端倪。
“今日怎么这么老实?”
元隽回来时已是午夜了,一进帐便见她安安静静的倚在榻上看书,模样竟还有些乖顺,他褪了披风随手一扔,含笑走过去,“白日里,我还当你给姜彦缨诊治完了之后,会去府衙寻我的。……对了,我回来之前,铁壁侯府的人传话,说是姜彦缨已经醒了。”
“我的医术,自然不会错。”她说着,搁了书卷坐起来。
“白日我同袅袅在四周围逛了逛,挖了些鲜笋、蕨菜,晚上包了些笋蕨馄饨,你饿不饿?我备着水呢,下一碗给你暖暖胃可好?”
透过如豆的灯火朝她望去,氤氲的光芒,仿佛也在她周身踱了一层光,他忽然有了种感觉——这军营大帐,原是最不安稳的地方,此间,却真似一个家了。
元隽含笑应好。
不多时,罗汉榻上摆起了小案,他吃着她煮的馄饨,时不时还夸奖两句好吃。裴筠筠就披衣捧茶,坐在他对面看书。
等他那边吃饱了歇好了,她才问起:“怎么样,审了一整日,都审出什么来了?”
“翟温自尽了。”他声色平平,道:“在堂上。”
裴筠筠一愣。
“怎么回事?”她蹙眉道:“上次才出了行刺之
事,再严加防范十倍都不过分,这回倒好,他那袖箭不往别人身上射了,索性直接了断了自己?铁壁的守卫都是吃干饭的不成?”
她是真有些动气。其实,该调查的,叶檄都已调查个大概了,翟温在她眼里,已没有多大价值了,可是这堂上自尽之事……幸亏这回翟温是自戕了,否则,他若是再打一次行刺的主意,后果不堪设想。
“他口中藏毒,见血封喉。”元隽说着,摇头一叹,“可见冯太尉当真是手眼通天,翟温人在铁壁府的铁牢里圈着,太尉大人这都能递进去东西、递进去话。”
翟温此人,按底下人的调查来看,原是冯夫人早逝兄长的学生,与之自来熟识,明面上虽同磐石少有往来,但私下里,却素来与冯太尉勾连不断。
——又或者说,是与早死的冯冕臭味相投,沆瀣一气。
他当堂欲行刺羽雁王的理由,或许还可以归类为,心知自己命不久矣,临了有心拉一个赚一个,顺带给他那位故友报了仇。可这会儿这摆明了灭口般的自尽背后,恐怕就让整件事情都变的不那么简单了。
元隽道:“铁壁侯两番失责,先是危及郡王性命,后又有重犯当庭自尽,实在不能姑息。我已命叶檄亲自带人去排查铁牢中所有侍卫看守了,即便我不指望揪出个人来能给冯通定罪,但至少铁壁的安全得保证了。”
裴筠筠哼笑道:“那恐怕不止要
排查铁牢中的侍卫罢?”
他无奈一笑。
“还有,”顿了顿,他继续说道:“翟温之所以会突然自尽,是因为他自尽之前,曾被我乍出了一句话。”
“什么话?”
具体什么话,元隽没有转述,只将那话里的意思告诉给她:“归根结底一个意思,这回铁壁暴乱之事,背后的推手,应该就是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