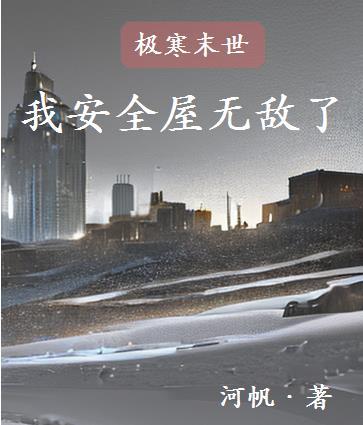笔趣小说>风云下一句是什么 > 第246章(第1页)
第246章(第1页)
如玉急忙勒马:“没有啊,正因为还没回来,才将婚事不得不拖到了明日。”
彦卿一听,登时心慌:“不好,那些护国军不是在修建兵防,是薛蕤的障眼法,是围剿!当初他围剿庞显反军便是如此布兵!我急着送宝物回来,竟未反应过来。”说罢,将身前包袱中一块方匣交给如玉。
如玉打开,内里正是传国玉玺。
“数日前,张宝莲在天龙寺莲花池前与拓跋英作戏,以让拓跋英为她祖母之死赎罪为由,将此物托付,恐怕那时她已察觉到薛蕤野心。”彦卿解释道,“拓跋英跪在冰水中,冻伤了双腿,行动不便,我已将她秘密送回岚州小雀岭养伤,她醒后觉得此物放在云隐只怕迟早被人抢去,便叫我趁还无人发现时赶快送回义父手里。我想…这也是张宝莲的本意。”
如玉拧紧了眉头,难道薛蕤已知此物?
彦卿焦急:“眼下如何是好?义父与五哥先前率军在前冲锋,已被庞显折损许多,而薛蕤的护国军却大多是来自星海的红巾军,熟门熟路绕在庞显后方,反倒保存了大部分实力,他若有心陷害,以多欺少,义父与五哥只怕要吃暗亏!不如尽快通知大哥和二哥从陇、代两州搬兵来救?还有,我这就回云隐重新整军,到时南北夹击,必救出义父!”
“等等!”如玉却摇头,“宝莲既将此物交出,说明绝不会是她告诉薛蕤,宝莲的父亲从头到尾都不知道真玉玺的所在,这也多亏宝莲祖母安排。你说,这天下,还有谁会告诉薛蕤真玉玺的事?”
彦卿:“沙月王?难怪他将皇帝掳走之后,并未下过一道诏书,他自知名不正言不顺…他要利用薛蕤!”
如玉:“我若是沙月王,绝不能在此时眼睁睁看着薛蕤与封云联军,便只能从薛蕤下手,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薛蕤:封云仍手握真玉玺。”
彦卿:“薛蕤竟不是为了张宝莲么…”
如玉:“宝莲与隋护卫之间根本没什么,薛蕤是知道的,他若要追究,不会拖到现在才出手,只怕他是在等沙月王沙月王的下一个目标竟然是雾原我们绝不可从陇州与代州调兵!”
彦卿:“好一招围剿!”
如玉想了想:“老大与四哥尚在陇州,必有对策,沙月王绝占不到便宜,便只得调转兵戈,又朝南去。拓跋英受伤,其父又年迈,彦卿,你还是快回云隐,务必加紧西线防御工事!至于薛蕤,我自有办法对付。”
五百铁骑
星海,薛蕤大营。
宴席从午间喝到夜晚,期间无论封云与彦邦如何推脱,仍架不住薛蕤与手下不断送上好酒,轮番敬劝,终于撑不住海量与盛情,昏昏倒去。
当夜,雾原军营便被薛蕤手下包围。
封云与彦邦被押送暗牢中看管。
次日,封云昏昏沉沉醒过酒来,却发现自己手脚被铐,身旁是各种刑具,瞬间明白,悔之不及:“薛蕤害我!”
牢头见他醒来,急派人去请薛蕤,而后转身对封云却面露难色:“封大将军,小的就是个牢头,若不是上面吩咐,绝不敢将您押在这里小的敬重雾原军,更敬重您,劝您待会儿莫要硬扛,这些刑具可是会要人命的!”
封云:“这是哪里?”
牢头:“海晏府,原本是庞显的一处外宅,自薛将军回来,便将这里改成了牢狱。”
封云:“雾原军如何了?”
“原谅小的不能再说了,薛将军知道会杀了小人…”牢头将一碗清水递送到封云嘴边,“喝了这水,就算小的先跟您赔不是了。”
封云呵呵笑了一声,用嘴叼住水碗,仰起脸,半喝半洒,而后撇碎在地。
薛蕤赶至,果然不由分说便是一顿拷打,所幸那牢头下手既重又轻,是个行家,虽打得封云皮开肉绽,满身鲜血,却并未伤及筋骨。
封云竟咬牙,不出一声。
“呵呵,解气!”薛蕤冷笑,摸了摸自己脸颊上的疤痕,“谁能想到封大将军还做过我的护卫呢?隋护卫骗了我,还想一走了之么?”
封云:“你要杀便杀,何必啰嗦。”
“你想速死?没那么便宜!”薛蕤挥了挥手,示意那牢头往封云伤口上泼撒盐水。
封云终于疼出了声。
薛蕤高兴了起来:“你当初带走莲儿,是为了拿走那东西吧?嘶…沙月王说那东西还在你手中,不如你交给我,我一定放了你。”
封云皱着眉头:“你竟也敢要那玉玺?”
薛蕤一巴掌扇过去:“你这副语气,难道我不配?我最瞧不起你们这些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人!”
“呵,可笑,莫非你娶张姑娘,只是为了那东西!”封云向他吐出一口鲜血唾沫,“你的确不配!”
薛蕤掐住他的喉咙:“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封云无法挣扎,闭上了眼,心中遗憾不能再见如玉最后一面。
“将军!不好了,横谷山脉突然翻下来一股羌厥骑兵,也不知何时溜进了越州边防,正朝青州城门口杀来了!”信兵匆匆来报。
薛蕤这才松手:“羌厥兵?来了多少?”
信兵:“大约五六百!个个骁勇,杀得咱们措手不及,咱们的骑兵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步兵更近身不得。”
薛蕤疑惑:“越州,莫非是从那老星海王的没落商道而来?他们此时来青州做什么?”
信兵:“为首那人说,他们是来与薛将军做生意的。”
“哦?”薛蕤看了看封云,笑了笑,“呵,看来不只我想要你的项上人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