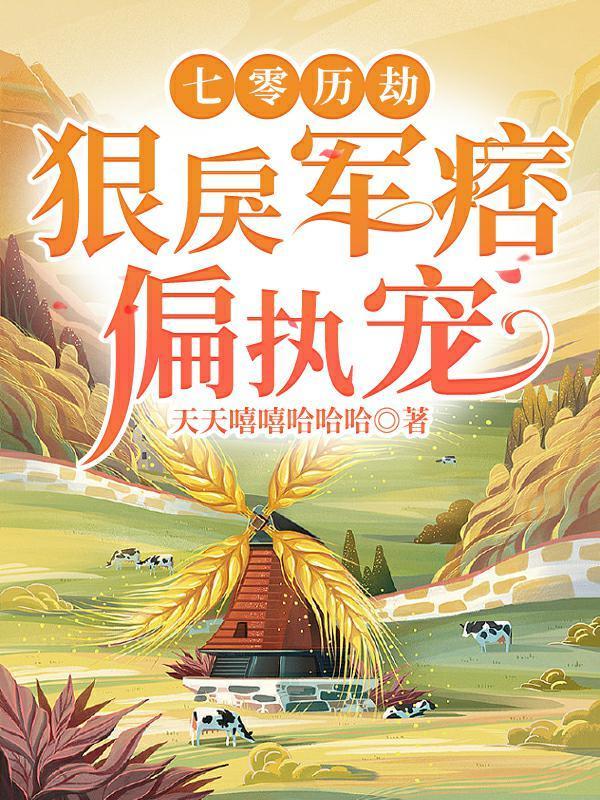笔趣小说>万人嫌小聋子嫁给渣攻舅舅后子午墟 > 第65章(第2页)
第65章(第2页)
他天生骨硬筋硬,不似女孩子天鹅绒一般的柔软,摆弄起四肢来横平竖直。
不像跳舞,倒像在做中学时的广播体操,他自己看了都觉得怪异,像扣了电池的小机器人,一瞬间垮掉。
盛愿不死心,清了清嗓子,换了副细弱的声线,微微出一点声音。
“啊”
他蓦然一怔,猝然间止住声音。
不管如何修饰,都改变不了他与生俱来的清冽少年音,甚至连介于男女之间的中性感觉都听不出。
盛愿被自己的声音惊到,仿佛从醉意中猛然醒神,面露茫然。
他颓然的弓起背,蹲在地上,整张脸埋进手心,指缝间溢出一声哽咽。
他无声的抽噎,滚烫的泪从手腕淌下,肩膀在夜风和月中,仿佛一根细弱的蒲苇在风中颤抖。
为什么要穿裙子,为什么要戴假,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他通通都想不明白。
兴许,这场瓢泼,早该停了。
许久,房间里的抽泣声止住。
他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把捞起地毯上认不出名字的洋酒,仰颈咕嘟咕嘟灌下。
来不及吞咽的酒液顺着颈项滑落,被领口的布料吸走,味蕾几乎被酒精麻到尝不出任何味道。
他抬手一抹下颌的酒液,酒瓶从他的手中掉落,清脆一声。
他只剩下最后一个夜晚,被讨厌也好被赶出去也罢,他不在乎了。
接着,盛愿头也不回的推开门,径直走向走廊尽头的黑暗。
酒精给他壮了胆,也麻痹了他的思考,现在他的脑子里只清楚一件事。
从走出这扇门开始,他已经完了。
-
牧霄夺的卧室没有落锁,轻轻一旋就推开了。
他的房间和他本人一样,充满着禁闭的私密感,厚重的窗帘透不进一丝月光,仿佛一座置于地下的幽暗密室。
这恰到好处的黑暗,成为了盛愿最后一层遮羞布,让他可以坦然地走进房间,来到床前,不担心会暴露。
牧霄夺一向睡眠浅,今夜却睡得格外沉了些,或许是一整月不间歇的奔波辗转,使他生出些许疲倦。
睡意朦胧间,他感觉到身侧的床垫微微下陷,出细微的声响。
他缓缓撩开眼皮,只那么片刻间,就被从天而降的丝扑了满脸,他从迷蒙中瞬间惊醒,下意识推开伏在自己身上的人。
“砰!!”
“唔……”
盛愿摔得头疼,他本就醉得像滩烂泥,现在更是直接化在了床上,两眼冒金星。
牧霄夺则是单手揉捏眉心,久久没有言语。
说实话,这个场面还是有些人的。
大半夜,一个穿着艳丽红裙的长女鬼匍匐在自己身上,简直是恐怖片桥段。
如果不是盛愿忍不住出声音,这一秒他已经不在床上了。
“……阿愿。”牧霄夺声音还挂着清醒不久的沉哑,“一个人睡不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