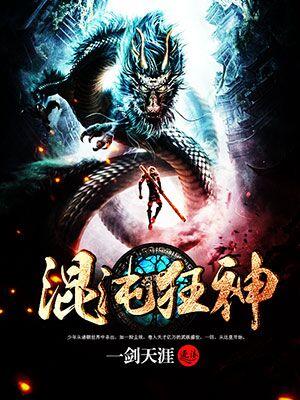笔趣小说>江山聘你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 > 第一百零七章 第一百零七章(第1页)
第一百零七章 第一百零七章(第1页)
齊曕進了渡坤宮內殿,御案上一如往常堆滿了摺子,但難得,姜琸今日沒在看摺子,而是站在御案前,負手而立。
聽見腳步聲,姜琸沒轉頭看,只輕聲說了句:「來了。」
「臣齊曕,參見陛下。」
齊曕躬身行了禮,姜琸沒說免禮。他默了會兒,突然問了一句:「那天,你看見朕了吧。」
齊曕直起身,眸光微動:「是。」
姜琸轉過身,看他。
兩人的目光對上,姜琸道:「趙焱的念頭,或許是朝中許多人知道真相後會有的念頭,他所說所做,朕聽著看著,並非全然安之若素。在那天之前,朕亦想過,自己是名不正言不順的竊位者。」
姜琸走到御案後坐下,指了指一側的方椅,示意齊曕:「坐吧。」
齊曕走過去坐下,姜琸續道:「在那天聽見皇姐的話之前,朕其實想過,將來等皇姐有了孩子,就把皇位還給姜氏。」
內殿早備好了熱茶,齊曕偏頭,看著熱霧從茶盞里升騰而起。
姜琸略有些狼狽地避開了視線:「朕知道,不管她身邊將來是誰,都絕對不可能是朕。她會有疼愛她的夫君,會有可愛的孩子……」
齊曕與御案後年輕的帝王對視,良久,移開目光。他朝門外看去,隔著晃動的氈簾,時隱時現能看見幾點雪色。
「齊曕。」姜琸抬手止了他的話,「你不必說什麼「愛美人不愛江山」之類的話,朕不信。」他直視著他深邃的眸,天子威儀傾軋,「你放棄權位,背叛晉國,這些都可以是為了皇姐,可是在唐城,你對朕捨身相護,朕卻不信是你愛屋及烏。」
齊曕放下手,略坐得端然了些:「陛下直言就是。」
「什麼樣的答案能讓陛下滿意呢。」齊曕問。
「臣是來謝恩的,陛下同臣說這些,是為何。」
好像困於暗室的囚徒守著一盞孤弱的燭,乍起一陣風,那唯一的光滅了,水盡山窮,囚徒只能與黑暗融為一體。
姜琸抿了抿唇,神色冷峻:「朕知你和皇姐相愛,但若今日你不能給朕一個滿意的答案,朕就不能放心把皇姐交給你。別以為朕不敢殺你,畢竟,你也是知道朕身份秘密的人。」
「臨幸后妃,為皇室開枝散葉,是朕的責任,推脫不得。」
他沒答一個字,卻又好像什麼都答了。
齊曕聞言,抬頭看他,唇邊露了一點笑意,眸子裡是雲淡風輕。
他說這話時沒自稱「朕」,好像還是當初在晉國,在清河侯府那個寄人籬下的皇子。
姜琸看著他,眼底流過一絲羨慕,用極輕的聲音說了句:「其實,我的心思,你一直很清楚,對麼。」
姜琸目光飄忽,像是在虛空中看到了自己美好的憧憬,他話音略停頓,那些虛妄的畫面便煙消雲散,他只好回到現實:「朕本想著,將來皇位要給皇姐的孩子,如今後宮空置便也無妨。可是……皇姐不會有孩子了。」
齊曕伸著手,稜稜的長指在茶霧的熱氣上蹁躚,指尖染了茶韻,他將手指放到鼻尖下,嗅了嗅。
齊曕無言,看向姜琸的目光里,總算帶上了幾分認真。
姜琸看著他的舉動,只以為他嗅的是茶香:「……朕有話問你。」
「自然是——」
時至今日,他還記得在唐城石室的門外,他意外聽見她說的話時,那種茫然又無力的感受。
「你為何幫上殷?」
「真話。」姜琸答。
齊曕起身,緩步走到殿中央,兀地朝著姜琸拜下去,謝恩。
姜琸神色複雜,靜看著他。
齊曕謝了恩,起身往殿外走,快到門口之時,他停下步子,背對著姜琸道:「其實,答案很簡單:我從未背叛過晉國。」
「什麼……」
「因為,我本就是上殷人。」
說完,齊曕邁步出了內殿。
氈簾掀開又落下,灌進一簇冷風。
御案後的姜琸難掩愕然,面上的驚詫猶如被寒風凝結。
——晉國的清河侯,怎麼可能是上殷人?!
——除非……他是假的,根本不是真的清河侯。
「……比起封官給他實權,我想,他會更想要那座宅子。」
姜琸猛地瞪大了眼,一個荒唐的念頭閃過,他只覺五臟震駭。
*
齊曕出了正殿,去偏殿的時候,姜嬈已經趴在桌上睡著了。
馬車上被折騰得厲害,又起得早,睏倦也是難免的。
抱秋要去叫醒她,齊曕抬手制止,自己走到她邊側另一張椅子上坐下,等她睡醒。
姜嬈這一睡,就是兩個時辰。
睜開眼,狹窄的視線里只抱秋一人,她起身,剛一動,胳膊上立馬一陣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