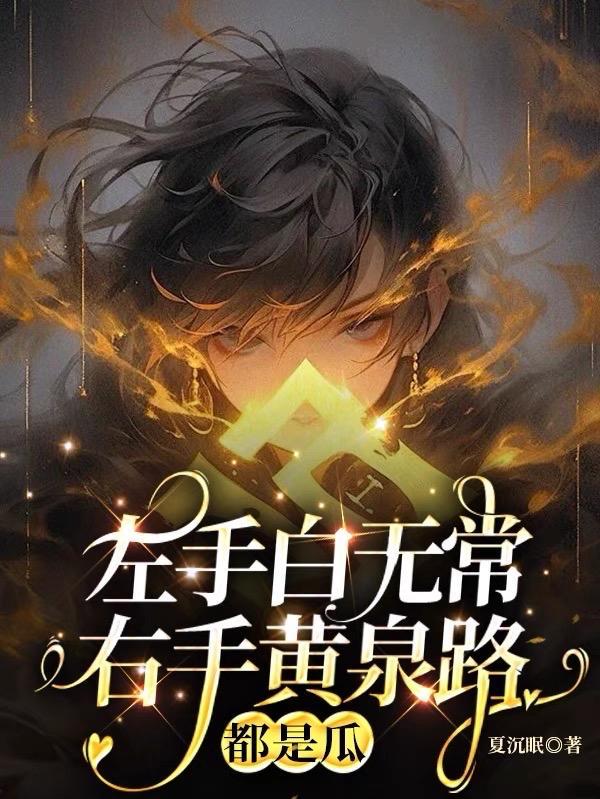笔趣小说>红楼之林家庶长子悠闲 > 第229章(第1页)
第229章(第1页)
三日后,皇帝淳于锋在圣心殿召见闵王淳于钟。
堂兄弟多年不见,淳于锋也不摆皇帝的架子,亲切地问了堂兄的近况,听说他为了避难,在远隔重洋的蛮夷之国住了八年,不禁十分怜悯,叹息道:“宗室操戈,以致骨肉相戮,朕心实不忍。堂兄及其余宗室子弟既然诚心来归,朕自当好生安置,也好告慰昔日皇祖父皇祖母之忧心。”
淳于锋又问及堂兄怎么没带侄儿侄女们一起过来,淳于钟告诉他未曾娶妻,淳于锋马上说要为他安排婚事,被淳于钟谢绝说:“臣本断袖,无意婚娶,且有知心人相伴一生,不敢烦劳圣心。”
淳于锋摸着下巴苦笑:怎么咱们淳于家近年尽出断袖啊,得,要把这个事情和小弟说说,好敲打敲打他,别跟这人一样误入歧途。本来宗室人口就够少的了,还这么多人不结婚不生孩子,唉。
淳于锋即改淳于钟的原封号“闵”为“诚”,迁淮南之风景至胜之地为王,享俸禄万石。
等淳于钟谢恩退下后,淳于锋便马上将三弟淳于铤喊了来,语重心长地说:“你看看刚才来的这人,当时他的情形和你一模一样,也是皇帝唯一的弟弟,只不过,他是庶出,你是嫡出。他当时就是胸无大志,玩啊玩啊玩的,就玩成断袖了,现在这个惨啊,你可不能学他。”
淳于铤比淳于锋小六岁,比淳于钊小八岁,现在正是无忧无虑的年纪,他比较怕大哥淳于钊,对二哥则总是嬉皮笑脸的,就是二哥当了皇帝以后也是一样。此时淳于铤果然对皇兄的谆谆教导不以为然,痞笑着说:“皇兄,你这比较得不对啊,他喜欢男人才会成断袖,我又不喜欢男人。”
淳于锋没好气地说:“你是不知道厉害。你们在外面玩,开始是女人,可是良家女子都不抛头露面,你们玩来玩去就只能玩些风尘女子,慢慢地就摸索到小倌儿身上了,甚至好友同窗身上,渐渐地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总之,在外面游手好闲是要出事的,弄不好就断袖了。”
淳于铤唇边一抹欠揍的坏笑,反问道:“那大哥呢?他可是从来没有在外面游手好闲过,怎么也断了呢?”
淳于锋骂道:“大哥的事情你也敢胡说,你……”
淳于铤马上说:“不敢不敢,不过有大嫂那样的风貌,断了也是人间美事一桩啊。”
淳于锋气得磨牙:“你这该死的真欠捶一顿是吧?什么大嫂,你胡说什么?”
淳于铤反而挺直了胸膛,说:“不是大嫂是什么?哼,你不在心里敬他为大嫂,等大哥回来我告诉他,叫他来捶你一顿。”
淳于锋忽然福至心灵,从来都不擅言辞的他伶牙俐齿地回了一句:“大嫂不是放在口上说的,是放在心里敬重着的,你小子趁着大嫂不在,妄议他的事情,哼哼,等大哥大嫂回来……”
淳于铤马上拉住他的袖子求饶:“好嘛,我知道错了,皇兄饶了我吧,别叫他们知道。”
此时,正在泰山看完日出下来的林默忽觉耳朵好痛,便对淳于钊说:“肯定又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了!”
淳于钊亲昵地摸了摸他的耳朵,说:“等我回去收拾他们!”
林诸妹妹乃至贾府诸人的番外
安国候府不日将要竣工,淳于钊高兴得很,谁知林默一句话就浇灭了他期盼在爱人面前献宝的热情。
林默说:“太好了!赶在它落成之前,我要回扬州去把弟弟妹妹们接来。”
晴天霹雳。
朕修侯爷府是为了我家睿儿住着舒服有面子的,可不是为了他家那两个拖油瓶!
林默看着他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就好笑,走过来摸摸他的脸,说:“我妹妹快要出嫁了呀,你讲点道理好不好?这些年我一直跟着你东跑西跑,都没有好好陪过她们,现在有了新房子,正好让弟弟妹妹们住上一阵子,然后我妹妹可以从侯府风风光光地出嫁。”
淳于钊反握住他的手,把人家的手死按在脸上蹭啊蹭地求疼爱,委委屈屈地说:“你哪有功夫跑这一趟腿子啊?再说,你走了,我觉都睡不好的……”
见过大型犬类撒娇弄痴是什么样的情形吗?就类似咱皇帝陛下现在的样子。
林默说:“我就一个月就回来了。”
淳于钊悲愤地说:“一个月!!!那可叫我怎么过啊?不如……我派一队锦衣亲军去,保证平平安安把她们姐弟两个带来你面前。”
林默摇头说:“不行。我妹妹早年受过一些惊吓,看到锦衣卫啊锦衣亲军就害怕。”
淳于钊摸着下巴,想了个折衷的办法来,“那叫我二弟去跑一趟吧,亲王去帮着接你家人,这脸面可不小。正好二弟也想去观赏江南的风光呢,一举两得。”
林默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说:“你弟弟?你确定没搞错?你弟弟一个外男去接我妹妹?那我妹妹的闺中女儿的名声不是要被生生断送了?”
淳于钊嘿嘿笑着说:“什么外男不外男的?说得那么客套!睿儿,咱们现在可是一家人了,什么你的妹妹我的弟弟的,多生分啊。是咱们的弟弟妹妹!见个面有什么不得了的。”
林默懒得听他狡辩,直接决定了次日就走,没得商量。
淳于钊只好化悲痛为力量,夜晚化身为狼人,翻过去倒过来地折腾林默,还说是按着现在的频率一天做两次,一个月三十一天,就等于林默欠下了他六十二次,就算利息和零头忽略不计吧,六十次是必须以后补上的。
于是,可怜的林默为了回家一趟,欠下了一大笔肉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