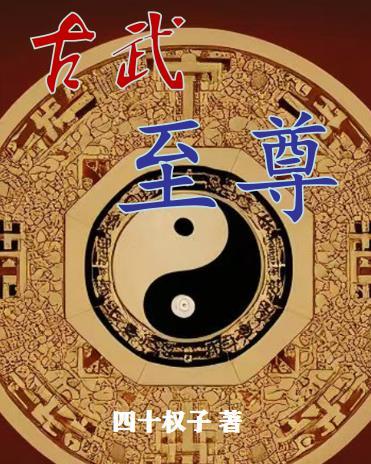笔趣小说>通房生存手册免费完结 > 第101章报复(第1页)
第101章报复(第1页)
曼曼到底还是打消了装病的念头。
她不想把陈老爷惹急了。
陈老爷那样的人,看似无害,可其实不知道手段有多毒辣,惹急了他,他不定在她身上使出什么更狠更直接更让她没法招架的手段来呢。
如果她病了,很有可能陈老爷把一切繁文缛节都省略了,直接把她剥光了塞到陈云方床上那她还不如留着一个健康的身体,保存点体力和精力呢。
及至陈妈妈准备了文房四宝,拿来了陈云正的家书,请她代为回信的时候,曼曼越确定自己的判断没错。
真是可笑,亏得她还以为自己也算是聪明的,可是不懂世情的她和陈老爷相比,实在是上不得台面。
她所做的一切,只怕陈老爷都当成了笑话在看呢。
曼曼读完了陈云正的家信,半天也没动。
管她是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还是做消极的抵抗呢陈妈妈气定神闲,很是坐得住。曼曼不言不动,陈妈妈也就不催。
如果苏曼曼是个蠢笨的,她根本不必费事。如果她是个聪明的,更不必自己废话。曼曼微微出神,也不知道在想什么。那就给她时间想清楚了吧。
曼曼的确是在出神,陈云正的书信,和每次的都不太一样。言语之间有些焦躁,书信也比往常要短了三分之一,他甚至在信尾抱怨不知是否天气渐欲暑热,余星夜辗转,月半不能成眠。
就这么一句,没头没尾。却更耐人寻味。
半晌曼曼才回神,歉然的朝着陈妈妈道“妈妈想必是不太了解,每次回信都是大爷口述之后再由我代为誊抄的。”
陈妈妈道“姑娘也不知道写过多少封回信了,就算大爷不在跟前,想必您也能倒背如流,何必再多此一举大爷出门了呢,归期不定老爷又急着给六爷回书,就怕他只身在外心不安稳。”
曼曼也就点点头,道“那我就勉为其难吧。”说罢挥笔一蹴而就,撂了笔,道“劳烦陈妈妈拿给老爷过目。”
陈妈妈小心翼翼的捧着信纸,道“是,奴婢这就去回禀老爷。”
陈老爷将曼曼的书信从头到尾看了数遍,确定没什么破绽,也没有什么隐语暗语,更是对她自己的处境没提到一点儿,才算放下心来,道“算她识时务,叫人去拿给言瑾,交到驿丞,尽快转交到言直手里。”
写了回信还不算,陈老爷又命陈夫人挑了两个出挑的丫头,附带自己手书一封,着管事星夜起程去找陈云正,只说是拨给他用来服侍他的。
悉数安排完,转眼也就到了陈云方纳苏曼曼的吉日。
曼曼这些日子反倒平稳了下来。她就是一条鱼,被刮了鳞,剖了内脏,洗沷干净安放到了砧板上,就差最后一个步骤了。只要明寒寒的菜刀举起来,陈老爷一声暗示,咔嚓一声,这刀就会把她剁成两半,放入油锅,放入葱姜蒜,再用沸水蒸煮,她这道菜就算是做熟了。
所以,她有点认命了。
心比天高,好像说的就是她,她从苏曼曼身上醒来,就一直自命不凡,总觉得自己好歹也是活过一世的人,不说大开金手指,在这个时空活的风声水起,但起码摆脱一个小小的通房的命运还是可以的。
谁想命运让她如此失望,又或者她对自己如此失望。
其实还是她过于天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不管哪个世道,女人都是弱者,尤其在这个时代,女人根本就不能称之为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尤其是她还只是奴才,连活着的尊严都争取不到,她又怎么可能独立自主,还妄想为自由开战
一纸卖身契,就把她压的死死的了。
曼曼被告知晚上要早睡,明天是吉日,要一大早起来准备盛妆华服。据说还要坐上喜轿,在鼓乐声中,抬着几个箱笼,从陈府的角门出去,在街上绕了两圈,才进陈云方的清凉居。
已经算是给曼曼足够的面子了。
坐花轿,穿嫁衣,抬箱笼,配鼓乐,这是娶妻才有的排场,她不过是个小妾而已。
曼曼再度看了看窗外那小小的一方院子,高高的院墙,在几十次确定自己爬上去再跳出去人不知鬼不觉的逃跑几率有多大之后,沉沉的叹了口气。
她转身回床上睡觉。
很快就有轻微的脚步声进来,替她关上窗子,锁死了插销。
这几天,对她的看管越严厉了,她甚至连出屋子的机会都被大大缩减。
陈妈妈的说法就是“左右不差这两天,姑娘暂且忍耐忍耐。”
曼曼也就笑笑,只安安稳稳的坐在屋子里。她要做的针线都做好了,放在一个小包袱里,没有什么事,她甚至连书都懒的看,常常是白天睡,晚上照料样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