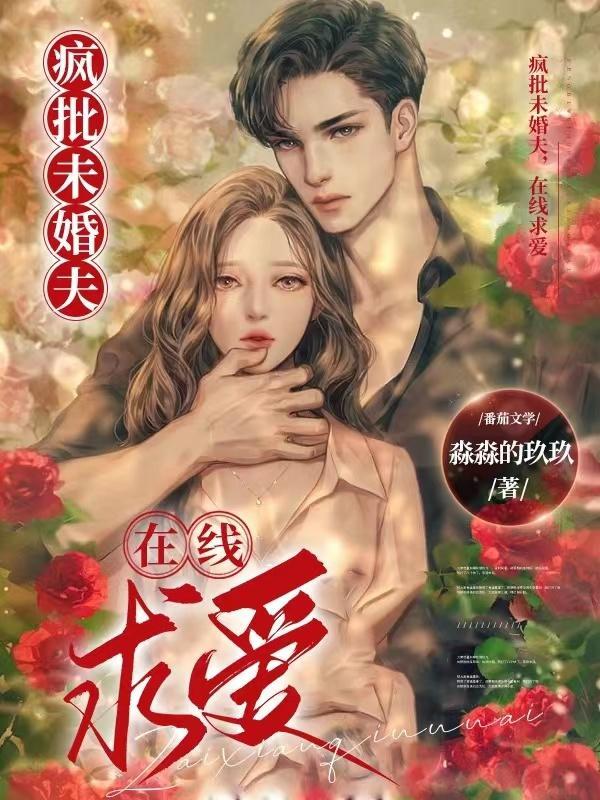笔趣小说>娇瘾难思卿 > 第61章 病发2(第1页)
第61章 病发2(第1页)
越苏嗯了一声,沿着石子路,越过草坪向深处走去。
“我来瞧瞧你。。。。。。”她道,顺道将抱着的锦盒放在石台上。
还留着半壶酒未曾收拾,越蕙就着壶嘴仰头倒下,虽然呛了一下,很快就咽下去了,傻傻笑起来,手中的箜篌未停。
还未来得及阻止,她已经将酒壶扔向了旁边的水池中,咕咚一声,很快就沉下去了。
凄离的声音再次响起,伴着箜篌,此时远比寒蝉凄切更为难受折磨,哪有半分“昆山玉碎凤凰叫”的壮烈。
一曲毕,越苏扶住她的身子,怕她不小心就要倒地。
“我哪有那么脆弱。。。。。。”越蕙拂去她的手:“只是想起来伤心事,心神不得安宁,唯有这箜篌之音,能让我短暂忘记一切。”
越苏心疼地要用手帕抹去她脸颊的泪水,可那泪水像不要钱似,断断续续流不尽。
“也许,过些天,会有转机也说不准。。。。。。”她只能空口安慰。
越蕙听了这话,突然惨烈笑了一声,语气中满是绝望:“不会了。。。。。。不会了,今日母亲告诉我,谢侯夫妻进京,第一件事是拜访了申家。”
或许是太过伤心,琴音断断续续,再不成曲。
越蕙终于不再弹,面无表情抚摸着琴弦,漫无目的几声撩拨,箜篌出嘶哑难听的声音。
她哽咽着继续道:“其实我与他,并不是初相识于洛霞山,而是去年七夕。。。。。。”
“你还记得吗,那天你刚好病了,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我就撇下你和二表哥去湖边放花灯。”
“碰见他在湖边垂钓,他的同伴问他,既然垂钓,为何不放饵,他说,他是在学姜太公,若有心甘情愿者,才是有缘之鱼。”
“我听了笑出声,便和他理论起来,道太公涓跪石隐崖,不饵而钓,乃心之所向并未为鱼。他问我,怎么知道他的心就是为了鱼,而不是为了其他?”
“后来我才知道,他听过我的名号,认出了我,与同伴做赌约,引我现身。”
“自从面见陛下之后,就有传言,陛下有意择我为太子妃,因此我需得谨言慎行,不可过分招摇,那日之后,我不再敢独自见他,可他托表哥送来书信,写了十余诗词,直言与我一见倾心,我。。。。。。更不知晓,他竟然去了洛霞山的菊宴。”
“那时候母亲病了,而我既无能为她治病,又无法为她分担家事,深感愧疚,谢姜便时时安慰我。。。。。。”
她说着说着泣不成声,仿佛过往浮现在眼前,他对她的呵护,相处的美好,都烟飘云散,不曾留下任何东西。
名扬侯和申家本就交好,有结为亲家的意图也是平常。
可她无法接受的是,明明爱着她,为何转头就能接受其他人。
他也有和她一样的苦衷吗?他也被父母逼迫不得自由吗?
可他那样的性子,宁撞南墙不回头,还是已经对她再无留恋,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婚姻?
直到此刻,她才真正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侯门之女,命运也由不得自己做主。
“越苏,我真羡慕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