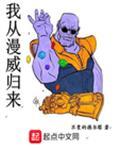笔趣小说>公子傒 > 第93章 同居(第1页)
第93章 同居(第1页)
急促的脚步声朝大门口奔来,鸡飞狗跳的。
温舒板着脸心想:“你这样的家伙,他不跑才怪。”
这些天处下来,她觉得司马峥像一条饿花眼的水蛭,狠狠地吸附在何子鱼身上,恨不能将他魂魄吸光。
她很愤怒:把人家弄得国破家亡的狗崽子,要是有点良心就该跪在山上那片坟前整日忏悔!住人家的祖宅,睡人家的身子,还要人不计前嫌时刻出现在眼前,哪来的脸?
司马峥抱着何念找出门来,视线落在温舒身上时猛窜起满腔杀意。
是不是这女人……
“哟,侯爷,您昨儿不是还显摆你俩情比金坚么?怎么着,牛皮扯吹太大,破了?”
司马峥狠狠刮了她一眼,吩咐人手将她看住,带着何念这个质子奔去山上瞧了一遍,又奔下山来,在村里四处询问。
不知不觉间走出榆阴,时不时遇到几个农人,司马峥一脸仓皇,逢人便问。
农人们看看他怀里的孩子,又看看他。
这么好的皮囊,这么好的衣装,一看就是城里有钱人家的公子哥。
城里人心花,像这般有钱有皮囊的家伙,恐怕是跟外人偷情,把家里人气走了。
大家看他的眼神立马不善起来,挥挥手:“不知道,没见过。”
司马峥不自觉收紧手,何念脸色惨白地看他一眼,忽然从他脸上估摸出自己的价值来:她是束缚何子鱼的一根铁索,只要何子鱼想逃,她就会被这人拎出来锁住何子鱼的脚。
何念眸光微闪,她断定何子鱼不会走,有点遗憾。
要是她逃出去,小叔叔是不是就自由了?
司马峥行尸走肉般在乡间长道上一步步往前走,暖阳落洒在身上,仍驱散不了身上的寒气。
他呢喃道:“去哪了?”
前方是条缓缓流淌的小河,深不见底,两边山峦在细微的水波中扭曲变形,他抱着何念,眼神直地朝河边走去。
鞋底踩过河滩上的老旧贝壳,轻细的碎响声在耳边响了一下。
何念黑白分明的眼睛静静凝视着司马峥,她从这人眼底看到一片地狱般的深黑,死气如潮水般从这双眼睛里涌出来。
她笑了。
将灵魂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人,纵使只手遮天,也不过蝼蚁尔。
她抱住司马峥脖颈,安心地闭上眼。
只要他俩都死了,小叔叔就解脱了,从此这世间,大概没有能威胁到他的东西了。
司马峥往水里抬脚之际,硬物在水波里划动的哗响声从远处缓缓飘来,司马峥不由得朝水波响动处看去。
两岸青山间,一身素白色布衣的人戴着斗笠,纤长细瘦的手持着长竿,衣袖往手肘处下滑时,露出白皙匀称的小臂。
随着他轻缓有力的动作,竹筏如水上的一片青叶,悠悠地滑过水中山影。
来人美目微动,一派平淡的眼神在看到司马峥怀里的何念时立马变得波澜起伏,几大杆冲上前,长张了好几次嘴。
何子鱼紧紧抓着竹竿,笑容惨淡。
“来喂鱼?还是想再给我弄个下马威?”
司马峥抿着唇,颤巍巍吸了口气,一脸戚戚地爬上竹筏,信口道:“来陪阿念玩,她说想捉河蚌……”
何念平静道:“我不喜欢河蚌。”
司马峥讪讪道:“我喜欢。”
说话间拉了拉长袍,将湿透的鞋面遮掩起来。
何子鱼被一口气堵得心塞,抄起竹竿在司马峥腿上抽了一下,司马峥低头摸着腿,心虚地抬起眼皮,飞一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