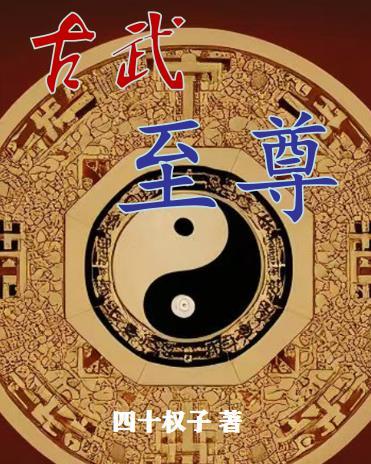笔趣小说>穿成反派大佬体弱多病的白月光免费阅读 > 第46页(第1页)
第46页(第1页)
这句话后她才堪堪反应过来,靳洛出生这九年,大半时间里,居然是傅容时一直在照看着他,她这个做亲生母亲的,即使是太子早亡,也不该就这样把孩子扔给他照料去,傅容时身体弱,这么多来,该有多难熬。
他的死,乔茭自知自己是要承担几分罪孽的。
正殿里的哭声凄厉而悲恸,乔茭走近了,才从他腰间的佩刀看清楚这是何人。
裴负雪狼狈地跪跌在地上,手指紧紧地捉着棺木边缘,撕心裂肺地哭着,一直以来积攒的悲痛,在确定傅容时真的死了的这一刻,全部爆了出来,他像一只无力的困兽,被牢牢地裹在网里,那种冰凉的感觉蔓延到他的全身,裴负雪甚至无法鼓起勇气再抬起头看他一眼。
只能死死地扣着棺木边缘。
乔茭微微皱眉,心情有些复杂,她上前道:“你为什么为他哭?”
裴负雪的哭声被这句话打断,骤然停顿住,他抬起头,一张脸上满是泪痕,眼睛空洞苍凉,看见来人后却猛地抓紧了腰间的长刀。
乔茭看了一眼他的那把刀,目光从被推开的棺盖上扫过,最后落在了裴负雪泪痕未消满是凌厉的脸上,她心里不知从何处涌入一团怒火,不禁嘲讽道:“你有什么资格为他哭?”
裴负雪咬牙,他一只手扣着棺木边缘,另一只手握紧长刀,虽是跪坐在地上,却仍旧谨慎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听见她的话,裴负雪瞳孔微颤,沉下声音道:“乔茭,你也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说这些话。”
乔茭冷笑道:“裴负雪,最没有资格的人是你。”
还没等裴负雪来得及想清楚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乔茭便嘲讽地继续说道:“你是不是觉得傅容时死因不明?便自以为是地先脱了自己的罪?”
她的声音陡然沉下去,像是怒极了,那张姣姣如月的温和容颜此刻也狰狞起来,她指着裴负雪,道:“他是心郁成结而死,他是因为你死的!”
心郁成结?
裴负雪全身猝然一抖,手指紧扣着棺木,嘴角溢出几缕血迹,脑子一片空白,所有的景象在他眼前逐渐模糊,所有过往的事情在他眼前走马观花一般掠过,璀璨星空投射出明亮的光芒,烧灼着他早已经千疮百孔的心脏,越来越沉下去,却愈觉得寒冷。
“裴负雪,最没有资格为他哭的就是你,你以为你作为罪臣之子,大景反贼,是如何安安稳稳地活到今天的?!”
乔茭越说越气,她看着深陷在痛苦里的裴负雪,心里为死去的傅容时感到畅快,忍不住想要说出更多,她把那些沉溺在过往的事搜肠刮肚,只想要这些话化作利刃,叫裴负雪更加痛苦才好。
“傅容时三番两次救你,你却在边关起叛乱,将他所有计划都摧毁,你知不知道他原本是想为裴家平反的?!”
“平反……?”
裴负雪脸上鲜血与眼泪混杂,他喃喃自语,“傅苒,他是想为裴家平反的吗?”
可是裴氏全族都已经被悉数斩杀,就算平反,那二百二十三口人的命,也终究是回不来的,他从没想到过傅苒居然有这样的计划,他从来都不知道……可是这样的事傅苒从来没对他说过,现在竟是乔茭来告诉他。
乔茭看着他茫然的表情,不忍地移开了目光,傅容时做的这些太不值了,她缓了缓悲痛的心神,继续道:“他告诉我,裴家全族都已经去了,剩下一个裴负雪他无论如何也得救,他说你也救过他的命,没道理在你落难的时候弃之不顾……”
“他不愿叫你去做军奴,可是没办法,他举步维艰地在朝堂上一点点地磨,想要寻找能洗清裴氏一族谋反罪名的消息,好不容易有了点痕迹……”乔茭说到这里,微微顿了顿,道:“太子殿下却意外驾崩了。”
“你在边关忽然掀起叛乱,坐实了裴家谋逆的罪名,把傅容时所有的计划毁于一旦,到这时候,他想为裴家平反,也没有理由了。”
乔茭忽然笑了笑,道:“你知道傅容时怎么说?”
裴负雪仰头怔怔地看着她,嘴唇微动。
“他说他还要救你。”
乔茭的眼中已经有了泪意,声音凄凉:“他给你安排好了的身份,只要边关的裴负雪死了,他就能瞒天过海,把你弄回来,去掉你的奴籍,你还能好好活着。”
裴负雪紧咬着牙关,不知不觉间,泪又落了满脸,他跪坐在那里,张了张口,却觉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不出一点儿声音——他失声了。
所有的痛苦无法宣泄,全部聚拢在了胸口,这一件件他不知道的事情浮出水面,他却像溺水一般沉到了冰冷的河底,吊起的铡刀就在他的头顶,他不想叫乔茭再说了,他快要受不住了,可是裴负雪的心中有另一个声音在对他说——“痛苦就对了,这是你应得的”。
这才是真的报应,是他该受着的。
傅苒心郁成结,死去的前一天,他还在与他争吵,他说了那么重的话,甚至对他横加指责……
——裴负雪,你是不是永远不会相信我了?
裴负雪喉间酸涩,傅苒的这句话,是不是在向他求救?假如昨日他软下来态度好好的说,假如他能好好地听傅苒说话,原谅他,选择相信他,傅苒或许可能会将这些事全部告诉自己,他原本不会死的……
可是假若傅苒昨日真的告诉了他这些事,他会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