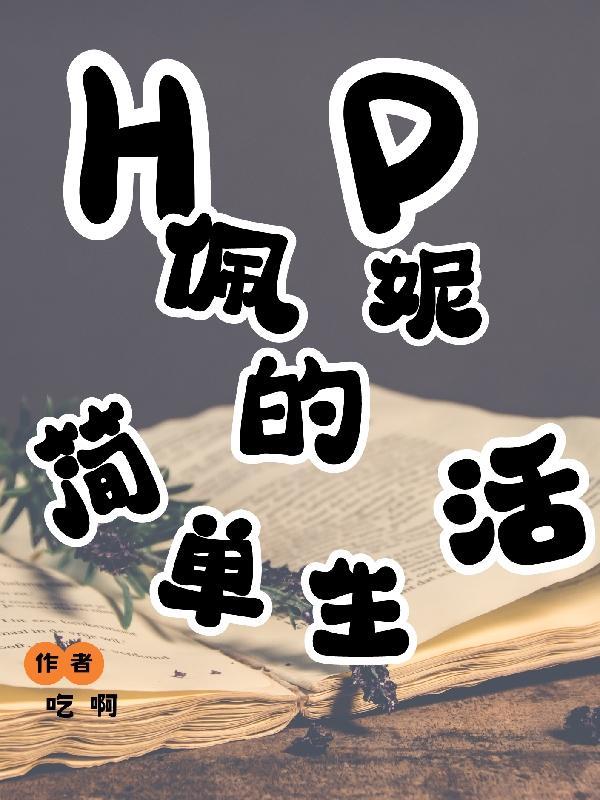笔趣小说>非典型例外北苍树全文免费阅读 > 第76頁(第1页)
第76頁(第1页)
路年把繩子在手上繞了兩圈,收好相機,隔著兩條欄杆就看見唐見疏扛了把掃帚在附近東張西望。
他身上還穿著睡衣,晨起的溫度並不低,路年順手拿了件外套給他披上,把人嚇得寒毛豎立差點沒跳起來打他。
「你怎麼起這麼早?在找什麼?我幫你。」
唐見疏提到這事就一肚子火氣:「沒找什麼,我倒要看看是哪些不要命的雞大清早叫個不停,睡都沒法睡。」
如果是什麼其他因素,憑路年多年偵查經驗肯定能幫上忙,但他現在總不能去把雞抓來教訓一頓,於是默了片刻,轉開了話題。
「……我昨晚跟你說的事,你想好答覆了嗎?」
唐見疏聞言一頓,背對著他沒回頭。
面前除了山就是樹,他把視線慢慢挪到地上,盯著一朵冬日裡還頑強開著的野花默不作聲。
路年昨晚問他以前那些事還願不願意聽他解釋,兩人從小到大,那些年披荊斬棘轟轟烈烈的愛情是他不管喝多少酒都忘不了的。
他在車上看見路年的時候就知道謝衍之為什麼會叫自己來,他沒法騙自己的心說不在意,所以昨晚跟他進了屋,把兩人分隔四年的原因剖析得徹徹底底。
誰都沒忘記,誰都沒有錯。誰都有苦衷,但誰都沒有先低頭。
「我其實——」
「早啊,都站在這裡幹嘛,還不去吃早餐?」
唐見疏剛要開口就被謝衍之的招呼聲喊得緊急剎車,不得已把沒說完的話換了個底稿,正想轉頭懟他兩句,卻無意間瞥見季書辭脖子上的紅痕,倒吸了一口涼氣。
兩個半斤八兩的傷員都這樣了還能開葷呢,簡直可怕得很。
謝衍之掛在臉上的早安笑愈發燦爛,季書辭早上看到手腕包紮的繃帶時就知道謝衍之半夜醒過了,只是沒想到除了這處痕跡外他還給自己留了點別的記號。
他想著想著又盯了謝衍之一眼,後者心虛地轉開視線,只當沒看見。
唐見疏剛醞釀好的氛圍跟答覆被他們一攪合又沒心情說了,好在路年也沒強硬逼問出答案,垂下眼睫,回屋換了衣服就跟他們去餐廳吃早餐。
飯後四人默契地分成兩隊各自在山裡閒逛,從餐廳出來的時候,路年意味深長地看了眼謝衍之,謝衍之就猜到他有事找自己。
果不其然,晚上剛吃完晚飯,路年就發微信問他有沒有空來落山亭旁的咖啡廳坐坐。
謝衍之讓季書辭先留在場館看表演,走進咖啡廳一看,桌子上滿滿當當擺著大魚大肉,就差舉個牌子告訴他路年是有求於他了。
「路警官,你這是?」謝衍之抵著下巴咋舌,「我剛吃飽飯過來的。」
「出來玩就別叫我職業了,給別人聽到不好。」路年伸手示意他坐下,「沒打擾到你吧?」
謝衍之搖了搖頭,他跟路年基本沒什麼交集,約莫估計了一下,十有八九跟唐見疏有關。
「想問唐見疏的事?」
「是,我想你讓跟我講講他在國外那幾年的經歷。」路年也不跟他打啞謎,直白地說道,「我錯過了很多,希望能補回來一點。」
謝衍之意外他竟然這麼坦誠,他了解唐見疏,非工作擋的時候咋呼冒失,但其實很有自己的原則。既然他今天都願意單獨跟路年出去了,說明他們之間的問題起碼也解決了七七八八。
只是他不明白到底是什麼樣的誤會,明明幾個小時見上一面就能說清,可偏偏相互折磨了整整四年的時間。
他心裡雖然好奇,但人家的私事他不好瞎打聽。
唐見疏在國外的經歷真讓他講也講不出個所以然來,都說勸人學醫天打雷劈,醫學的專業課在學校絕對算得上小王,數量僅次於雙修的學生。
唐見疏每天都是教室、實驗室、宿舍三點一線,一周到頭也就周天能穩定出來放鬆放鬆。
大學的生活豐富多彩不假,可真到要開口說的時候又發現,滿腦子的記憶竟然找不到能下嘴的突破口。
那些瘋狂的青春歲月逐一在腦海放映,他伸手想去抓,碰到的卻是一團渾厚的虛影。
謝衍之挑揀了一些講給路年聽,但路年顯然不滿足這些片面的事情,他還想知道更多,想知道這四年唐見疏的每一個生活習慣跟脾性愛好。
謝衍之為難地喝了口水,他尚且不清楚兩人目前的進展到哪一步了,這些偏私人性的事情,即便路年要知道,也不應該從他的嘴裡知道。
他虛與委蛇的樣子也讓路年意識到自己失言:「不好意思,這些事我還是自己去問小疏比較好。」
謝衍之就喜歡跟這種懂分寸的人交流,感覺自己沒怎麼幫上他的忙,看著面前的慕斯猶豫了一下,試探地問道:「那這慕斯我還能吃嗎?」
路年不自然地扯了嘴角:「……你吃吧。」
謝衍之搓了搓手,想到唐見疏還是個視頻愛好者,便找出他的社交帳號發給路年。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就已經在上面更日常生活了,你可以去上面看看。」
十幾個夾雜英文的阿拉伯數字跳出屏幕,路年視若珍寶,微微點頭跟他道謝,想起什麼,又問道:「你跟小疏是怎麼認識的?」
「他救過我一命。」謝衍之道。
那時候他哮喘發作,身上的藥用完了,意識已經不清醒的時候被唐見疏及時從閻王殿門口搶了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