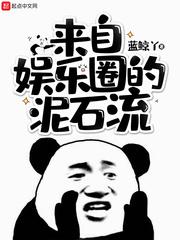笔趣小说>丫丫作者简介 > 第161章 至1094页(第1页)
第161章 至1094页(第1页)
嘘寒问暖的一阵忙活过后只知道沏茶递水、推送点心的海波比女孩还女孩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是奶奶用轻松的谎言替他消除了窘迫:“这孩子回来这段时间常在我面前念叨你,说把手上的事办妥当以后就去看你,这不,见了你反倒害起羞来了。”两个年轻人也相互乜了一瞥,害羞的程度也就不相上下了。
毕竟徐彩芹于世活跃,开朗善言,稍息片刻便有意向四处搜寻一下,一点也不打顿就改变了话茬,几句之后就直奔她想要知道的:“他爷爷现在还好吧。”“病了,在屋里躺着呢”娅琴的高贵气质被她削弱了。“哎呀,要是知道老爷爷病了我就早该来看望了”说着话还做出了假意要起身的动作。
娅琴摁住了她的肩膀如实地说:“屋里气味重,自从被误解以后就连下床走动的气力也是渐少无增,别人想躲还躲不及呐,有你这份心意就足够了,孩子,我替他谢你了。”
海波这时也跟着附言道:“彩芹同学,我也替我爷爷向你表示感谢!”“谢什么谢,我呀,是从同学那里得知你回来的,安置到了哪个单位也不跟别人说一声,还保密啊”她这就开始加快了度。
海波摇摇头颓废地挤出四个字来:“还没找到。”“哦,”小芹立马就转变成一副思索模样,活灵活现地眼神掠过仍然眯着笑眼聆听她俩对话的老人,然后又漫不经心的重新对着海波提议道:“你看这样好不好,回去我问问父亲能不能帮上这个忙。”
‘这可真有她的,说话做事就连一点风也不带透的,我这里生的事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我的孙儿要是能有她一半这样就好喽……’正思量着的娅琴听她还有这么一说便替孙儿开口言道:“小芹姑娘,那可真难为你了,我琢磨着也应该让他去工厂锻炼锻炼。”小芹对此并没有直接作答而是持续盯着芳心里藏掖着的心仪继续试探着:“如果行得通的话,那里很脏的,你愿意去吗?”海波这一次的应答是既利落又干脆:“愿意!能和你在一起再怎么脏、再怎么累我也愿意。”
一抹红霞飞跃而上,她不得不把眼光扫向老人像是在抱怨:“您瞧他,我在和他说正经事,既然他愿意,我这就回去问问父亲”说着便起身告辞。娅琴哪里舍得就这么让她离去,怎么着也要留她在家里吃个晚饭再回去,见拉扯无效时便指着窗外说:“那就再坐一会,外面雪下的正大,等下小些了再走行不?”
看不出来,彩琴的雷厉风行的性格愈了得了:“不行啊奶奶,四点半钟还有个批斗会去要参加。”经她这么一说,二人也只好哑口作罢,尴尬之下,海波倒也认真地对奶奶说:“批斗会的事耽误不得,我去送送她吧。”没想到,他的热忱也被她婉言谢绝了:“不用了,”她说:“一个人走得快,一有消息我就打电话过来。”
“电话不通了。”娅琴出的声音虽然很低,徐彩芹依然听得清清楚楚,她麻利地穿戴好三件保护、撑开雨伞就说:“那我就过来告诉你们,再见!”便如释负重的转身没进了天地一色的茫茫雪雾中,三步两步临近竹林前又回转身来朝目送她的两人再次挥了挥手,抛去了只有自个儿才知道的激情涌动,心里盘算的却是另一番如意:‘这一步走的非常完美,我一定要让他走出这泥潭’。而斜依在门框上的娅琴仍然盯着雪帘中没有身影只有几个即将消失足印的小道在低沉吟语:“没看走眼,果真是个不可多得的。”
之后,老刘听说姑娘来到这里的所为也对这位行事果敢的姑娘赞赏有加,只要见到老伴得闲的时候就想听听她和她家里的具体情况,并且夸奖海波很有眼光。假如老刘具有准确臆测,感知这对工人阶级的父女俩正视他如瘟神、千方百计想把海波从他的身边隔离开来,就抒不出这样的感慨了。
最最难熬的几天在不经意当中就这么又过去了。
四处奔走,处处碰壁回到大院还要忍受嗤之以鼻的不屑一顾,‘我不能再这么忍受下去,我要离开这让人透不过气来的鬼环境尽快融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这样的底气还是来自热血沸腾的思念为他鼓足了勇气:“奶奶,我想去徐彩芹家看看。”“你早就该去啦。”“嗯……”他做了一个囊中羞涩的动作,“奶奶这就去给你拿。”
他怀揣十元票子去了好几家供销社的水果门店,没有一家不向他搭售几个剜去坏掉的,他眼见再这样转下去时间怕是不够用时,才硬着头皮花了五元钱拎了两大兜大小不一的苹果见到了相隔几年头都有些花白的未来老丈人。高兴不得了的徐厂长与赵娅琴见到徐彩芹时的状态如出一辙,问长问短嘘寒不断,三菜一汤,外加小酒不多时就摆上了桌,不用问,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小芹的杰作。
本不胜酒力的赵海波凭借着血气方刚、年轻气旺在偶得新宠氛围之下得意忘形的举杯不断,更是海口连连。
父女二人便不失时机地鼓励他要提高思想觉悟、学好‘老三篇’,要认清当前形势,坚决彻底与当权派里的那些顽固派、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作彻底决裂。
酒醉心明的海波虽然领悟到了这些革命道理对他而言的真正用意,还是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不仅如此,还拍着胸口似有他人之过:“我在部队里也是这么说来着,如果小芹早把我家里生的事情告诉我,我就会当即做出了断,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小芹毫不迟疑就跟进道:“现在说也不算晚。”海波翻着白眼晃悠着脑袋看看他又看看她,仿佛是认可了所有,频频点头。
自从打开了这个豁口以后,海波便隔三差五的来到她家与小芹会面,虽然没有当面过多批判自己的爷爷,潜移默化的内心深处已经先将自己给出卖了。
当小芹问他有没有和双胞胎哥哥有过联系时,他竟然大言不惭的说:“我怎么能再认生活在修正主义国度里的哥哥为亲兄弟呢。”小芹转动着一双大眼睛当下就表扬了他:“你的进步真叫快,等进了工厂表现一定不一般。”就这样,同窗至今终于把埋藏在心底已久的互尊互敬恢复到了原点、消除了误解;日后擦出的日培夜修地爱情火花已然将炙热的红唇结合在了一起,一阵慌乱使小芹红着脸用疾如旋踵的度推开了罩在她乳房上的大手就说:“我们不能这样。”这样的恩爱举动在她看来是不能进行下去的,她是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绝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这样的苟且之事。
心急如焚、如被猫抓一般地赵海波脑子一片空白,似转圈又非转圈的反剪起手臂再一次嘟起了嘴唇向她贴去。
这一切他都没有告诉他的爷爷奶奶,只是一个劲传达了小芹及她的父亲和周围的工人阶级邻居们要他捎带给他们一些‘子虚乌有’的问候,以此平抑院内院外的巨大反差。
一个月不到,小芹的父亲顶住了来自街道和派出所的种种压力,并且写下了保证书,这才如愿以偿地把未来的女婿安排进了自己的工厂。对此,娅琴是千嘱咐万叮呤的对孙儿说:“现在找份工作很不容易,到了工厂只管埋头苦干,万万不可与人争、说大话。”在她看来,张副省长的提醒应该是经受得住历史检验的。
不仅如此,她还破天荒的领着孙儿、提溜着陈酒和麻油一起登门拜谢了他们父女俩。
高兴之余,她还把小芹的父亲在送行路上说的那句模糊不清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可以走在一起’的话反馈给了老刘。“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呢?”“当时没在意,也就敷衍了事的,之后才觉这其中像是有不明之意。”老刘便替她分析说:“无非指的就是两条路线问题。”“越说越让人糊涂,工厂里的,要那高觉悟作甚?”说到这里又不想再把他累到哪儿就改了口说:“哎,我说老头子,别看小芹姑娘年纪不大,懂得的事儿还真不少,居然能准确说出从沙皇时期到苏联政府占据我国土地的详细数字来。”尚未到万念俱灰地刘思敏听了反倒把头偏向了一边,一个深深的喘息过后出了近似哭一样的声音:“现在说这些还能有什么用,受制于人,受制于人呐。”
‘怕是糊涂了’娅琴翻身摸了摸他的额头没现有什么异样又责备起了自己:“都怨我图一时兴起说了这些不着调的,如今孙儿有了着落,我这颗心哪就像吃了秤砣一样稳稳当当的定下来了,这不一高兴就说了闲话。”“不要责怪自己,只要拖累不到他就是好事。”“……”“……”。
第一次走进蒸汽弥漫的猪毛处理车间的赵海波就被扑鼻而来的臊瘴气味熏的无章作呕,当场没晕过去也算是他的幸运。
新进工厂的员工都要经过这一工序才能调至洗毛、烘干、裁剪,而后才能理顺到制作产成品车间,赵海波当然也不能例外。
穿着连筒橡胶裤、手持长竹耙围着臭气熏天的煮浆池来回推来耙去,虽然脏水溅不到身上,换班以后任凭怎么冲洗,闻闻还是有那股怪味,几天下来就让他开始怀疑起了人生;难以忍受的天壤之别很快又改变了他的三观,甚至想到了逃避:‘就是四处流浪也比干这个好受’。
但是他的虚假傲慢与外强中干的勇气给他留下的除了观望没有其它,他害怕不被人正眼看待,更害怕小芹姑娘会离他而去,出了这个车间就咬牙切齿的佯作笑脸和别人打着招呼。
冬去春又来,他虽然用花言巧语得到了小芹姑娘的身体,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她全部的芳心,这就更加迫使他的不平衡的心态平生起波澜:‘难道非要让我那么去做不成?’他现工厂里的人现在对他都很好,唯独徐彩芹与他的距离反到是越拉越远——尽管还能隔一差三的聚在一起。‘不行!这一天一变的世界不能让我失去她,要是那样的话,我非死在那个肮脏的臭水池里不可’,他躲在一个无人踏足的僻静处抓耳挠腮地苦思冥想。
“对了,”他自言自语的自信计算又开始了:“我住进厂里不回去,看她怎么说。”心里兴奋着的脸上却没啥变化,他无聊地扔掉了初学抽剩的烟头,随手拨拉开附在残缺围墙上的旧年藤蔓,瞅着远处一群正在张贴大字报的活跃群体,迅疾间的一个既不新颖、也不陈旧的念头一闪而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能革我的命,我为什么就不能革他们的命!”随后,他的精神就是为之一振,状态也改变了许多。
这时的徐彩芹正把自己反锁在家里,‘我该怎么办?’的反复提问是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唯一摆脱不了的喜忧参半,也是她最为致命的阴影;结婚吧,海波一天没有和他爷爷划清界限她就不能和爸爸一起为他去背这个黑锅,不结婚吧,经血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了,这要是到了隐藏不了的时候那还不得让我去喝老鼠药啊。
“不行,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温吞水’的方式只能害了我和我的爸爸。”她相信她和他的爱情是甜蜜而又忠贞不渝的,若是让海波知道他就要成为爸爸时一定会做出决断的,刚毅而又可怜的姑娘走到这一步除了想到这些也别无它计可施。
“你好,赵海波同志。”在大庭广众的眼皮子底下小芹准时巡查到进料车间的门前,如常也向小赵打着招呼,海波的回答倒是比从前灵活多了一些:“你好,徐主任,我正有个想法想向你汇报一下。”正中其意的回答令她抬腕看了一眼手表就说:“十分钟后我在办公室。”她心里是有数的,因为从现在起一小时之内办公室是不会再有其他人到访的。
“说吧,需要汇报什么?”她的笑依然灿烂。
“亲爱的,”海波四处张望一下就坐在了她的对面:“我想把现有大字报里的内容添加一些新的内容。”“你的想法很新颖,我这就给你记下,不过,现在厂里的人手不足你是知道的,就算你不说,上面也会根据你的表现对你的工种做出调整。”说完就刷刷刷地记下了他的建议。
处心积虑的策略刚一出口就被她的几句话说的哑口无言,急忙满脸堆笑的说:“我这身上的味道你不会真就喜欢吧。”
原本流到嘴边的那些害羞话不知怎的一下子变成了:“划清界限这个问题可是拖不得呀。”“我…我想好了,我明天就搬来厂里不回去了,我要全身心地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你不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嘛。”徐彩芹的手落在了小肚子上:“我是说,革命讲的就是立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我的爷爷反正也快不行了……”
人之初的善念让小芹临时改了口:“那好吧,我会尽快答应你的要求,”她像是在忍,工作作风的味道却是越来越浓:“你回车间去吧,革委会哪里还有事在等我。”海波灵巧地冲着她就打了个响舌,一步三回的还挤了两次眼睛,而目送他出门的那张脸上始终都满挂着慰藉,当他的身影刚一消失,她就坐下来写了份请假条压在台面上就离开了工厂。冷静思索后的小芹瞧久了镜子里面那张不争气的相同人,眼皮跳动了几下便突然狂躁的捶打起自己的腹部,泄完以后也不整理一下自己拎起挎包径直就去了药店。
贴满了止痛膏的小腹到了夜里就感到了寒冰彻骨、难忍疼痛,痛的她咬破了嘴唇在床上翻来滚去,终于在后半夜感到大腿间流出了一股热流,几分钟过后她疲惫的拉亮电灯见到眼前的这一片狼藉非但没有生嫌,嘴角上反而挂上了一丝丝地惬意:‘谢谢老姐们平时说出的逗笑’,至此她并不知道采取这种手段堕胎是相当危险的。
虚汗还挂在脸上的小芹藏掖好了污秽的床单,又喝了杯红糖水就软弱无力的重新躺下了。
卸去了包袱又处于梦靥中的小芹还在惦记着赵海波:“对不起,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她怕是睡过了头”这一次做父亲的没有判断错。
当他叫醒女儿时却让他大吃了一惊:“你这是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都说女人天生爱说谎,这话一点也错不了,她揉揉眼睛坐了起来,说出来的轻松话就跟真的没有二样:“昨不是不舒服嘛,哪知夜里就闹起肚子来,跑了七八回,现在一点力气也没有。”
父亲心疼的问:“怕不是吃错药了吧?”小芹摇摇着头说:“没有,”然后就朝挪在床头边的凳子一努嘴地说:“就那么几粒都吃了,还是你原来吃剩下的,错不了。”“要不要去医务室瞧一下?”“不用,现在不痛了,休息一会就好了。”“那好,”粗心的父亲关心地嘱咐道:“早饭都做好了,吃饱了再出门,我得先去工厂了。”小芹在“嗯”的同又缩回到了被窝里。
经过好多天才恢复过来的徐彩芹在见到海波时仍同以往一样热情,只是再也不为他制造接近自己身体的机会。
他上次提出的那两个要求的其中一项已经得到落实,他心满意足的搬进了工厂,那个想出人头地换着法子早脱产他提意连想都别想,可是在这个错乱的时代,没想到的好运有时就是碰到个下三滥也是有机会能够实现的。
乐呵呵的徐厂长走进车间就大声喊开了:“小赵同志啊,你停下来停下来,”来到海波的近前时更是喜上眉梢的说:“快去冲洗一下换身衣服,派出所民警来电话说有几位从北京特意赶来这里的革命小将说要见你,这就赶紧过去哦。”没走几步又折返回来补充道:“如果他们不急着走,你就把他们带厂里来,也好让同志们听听北京的声音。”海波头点的跟小鸡叨米似的,心里却在嘀咕:‘北京哪里有认识我的人?真是’。其实厂长说出第二句话时,海波的双腿就抖动的一下,由于蒸汽的屏蔽才没被工友看见。
直到走进派出所,心里的忐忑才转变为喜出望外,原来这一男三女都是在哈尔滨念小学时的临班同学,那时他(她)们就能说会道!民警同志告诉他,与他同名同性的就有二十来个,如果不是说是由东北迁来的还真是不好找。
囊中羞涩的四位除了口无遮拦会吹之外就是一身不太清洁的时髦外表。
“你们也能穿这身军装成为红卫兵呀?!”几杯白干下肚后的海波搓着双手来来回回看着身着草绿色军装、腰束武装带还都佩有红色袖标的典型装束羡慕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