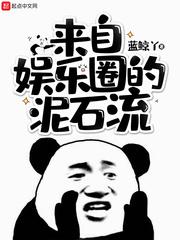笔趣小说>甄嬛传瓜尔佳氏死 > 第38章 线索(第1页)
第38章 线索(第1页)
安常在被带回住处禁足,宝鹃和其余太监宫女几人也被带去了慎刑司问话。
瓜尔佳文鸳与沈贵人、莞贵人从桃花坞出来后便一同回了揽月阁商议。
皇上多疑,且此事设计的滴水不漏,她们若贸然开口求情,说不定还会被皇上疑心有参与或袒护的嫌疑。
所以三人虽是心急如焚却,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再想他法。
好在眼下此事还有疑点尚未查清,一时半刻也不会处置了安常在,几人也好趁这个时间细细筹谋,如何为她洗刷冤屈。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虽说尚未定论,但安常在与余答应小产有牵连,且被禁足之事,不出几个时辰便传的沸沸扬扬。
余答应失去孩子本就伤心欲绝,听闻了这个消息更是悲愤交加,当晚就不顾自己刚小产完正虚弱的身体,便到勤政殿门口叩头求皇上为她做主,严惩安常在。
皇上本就因她小产之事郁郁寡欢,原本对她还有些许心疼和怜爱,可她这一闹却无异于让皇上更不堪其扰,烦心倦目。
可余答应在门口止不住的哭诉叩头,他终究还是念着她刚失去了孩子,不忍对其过于冷淡。
便当即下旨晋了她为常在以表安抚,并再三表示事情一旦查清了结果绝不姑息,还派人用辇轿让哭的梨花带雨的她送了住处,命了章太医为她调理身子。
后宫嫔妃都是素来喜欢瞧热闹不嫌事大的,眼看着安常在被禁了足,想着她再难翻身。
后来一连三四日都不曾召见过几人,众人便以为她们是受了安常在的牵连,所以晨昏定省请安时,自然对她们少不了一番冷嘲热讽。
她们三人虽明白安常在是被人陷害的,可恨现在无凭无据,且三人也不过小小贵人,无权干涉查问此事。
皇后呢,虽说主理此事,却不过是做表面功夫,自然是不肯事无巨细的盘查,所以以致于一连几日都丝毫没有任何进展。
…
好在华妃回过了神,私下悄悄派人传了话过来,说这件事的蹊跷之处便是在那招认的宫女身上,最好查清她素里日常与谁暗中来往,便明白是受了谁的指示,敢在宫里做谋害龙胎,攀污主子之事。
————————————
当晚夜深了,揽月阁中还掌着灯。
三人在殿内长谈。
瓜尔佳文鸳神情紧绷,无奈道:“华妃传话来说可以从那宫女身上找线索,我甚觉有理,便派了人去打听,可傍晚小晨子带回消息说那宫女已经自尽了。
沈贵人微微一愣:“畏罪自尽可是大罪,她难道就不怕牵连家人吗?”
“害怕?”莞贵人若有所思道:“她若害怕牵连家人,哪里还敢做这种掉脑袋的事。”
三人都能明显感觉得到,此事内情复杂,且背后之人心思缜密,什么都料理的不留把柄,若想还安常在清白,并非易事。
瓜尔佳文鸳不经意喃喃道:“若不是她想死,而是有人不想留下活口,以免深查下去牵连到自己,这才灭了口做出她自杀的假象呢?”
莞贵人看着她焦急的来回踱步,走的人差点晃花了眼,而后开口道:“可谁能在慎刑司对她下手呢,莫不是买通了里面的嬷嬷?”
沈贵人微微有些诧异:“我倒觉得,她畏罪自杀也有几分可能,毕竟她死了,谁还会为了这种不该宣扬的皇家内事去牵连她的家人呢?”
“余常在只要小产皇上势必会追查,她做此事时定然报了来日东窗事,自己免不了一死的决心。”
“但为了什么呢?总不能是贪图他人给的金银饰,便肯舍了自己的性命去做这种事?”
莞贵人与沈贵人正在各抒己见之时,瓜尔佳文鸳想起了问题的关键。
“她若是抱着来日事自己必死的决心,那幕后之人赏她的金银对她能有什么用处呢?”
这句话点醒了沈贵人,她顿了顿道:“你的意思是她为了自己的家人?”
瓜尔佳文鸳一手撑着下巴,一手摩挲着茶盖,淡淡道:“比方说幕后之人拿她家里的人逼她,她为了父母亲人,不得已只能舍弃自己的性命。”
沈贵人微一凝神,点头道:“这倒是有几分可能。”
“不若咱们细细查了那宫女的底细,书信告知家中派人去那宫女家中查探,或许能得到些线索。”瓜尔佳文鸳低头小声提议着。
莞贵人向来是心思细腻,能考虑周全的,毕竟安常在曾同自己一同朝夕相处过数日,自己对她家中情况还是很是了解的。
她嘱咐道:“此事暂时不要让安家知道,陵容父亲向来宠妾灭妻,自她承宠后,她父亲升了官职,她母亲的日子才好过些。若是让她家中知道了,不免引起慌乱,她母亲也少不了受人奚落为难。”
“是,嬛儿考虑的很周全。”
瓜尔佳文鸳想起原剧情沈贵人禁足时,有人给她的饭菜中下毒,试图让“假孕争宠”之时死无对证…
她当即起身,神色凝重的看向二人:“还有一事差点忘了,咱们务必想办法传信儿给安姐姐,让她饮食格外注意些,免得被人动了手脚。”
“对,那宫女死了,若陵容再出了事,别人也只会认为是陵容畏罪自戕。”
莞贵人沉吟片刻道:“只怕眼下后宫上下盯咱们三人盯得紧,唯恐找不出错处来,如何暗里传信于她?”
瓜尔佳文鸳眼角眉梢荡开了笑意:“或许华妃可以帮忙。”
“华妃协理六宫,在宫内一向有威望,若想传话进去自然容易得很。”
沈贵人的眼中闪过明亮的光芒:“是啊,咱们私下往来的谨慎,想来没人觉,自然也不会往她那里想。”
瓜尔佳文鸳接口道:“如此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