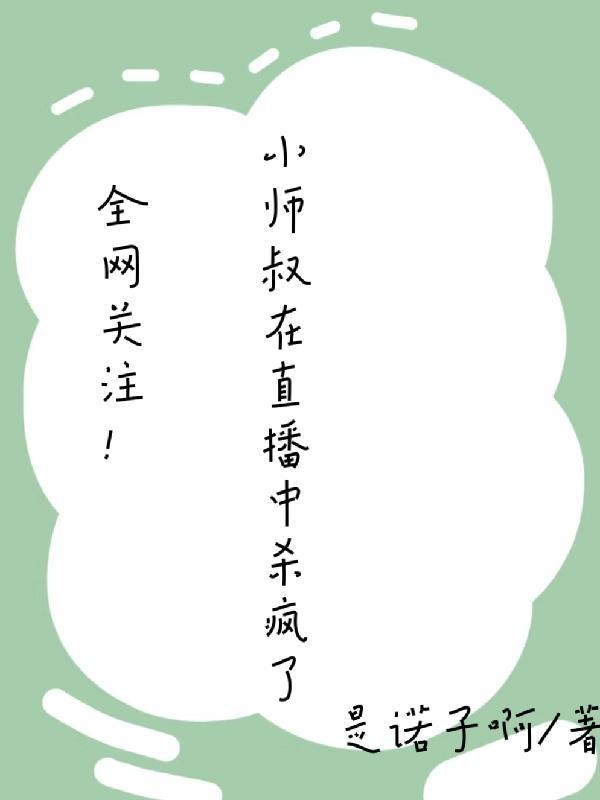笔趣小说>白月光黑化 > 第25章(第2页)
第25章(第2页)
是难得的,曾经对他好的人。
他罕见的直率问道:“师兄没有要见我的意思,又为何要将笛子赠来?”
“主家所命,不敢不从。”宣存礼摇头,神色惭愧歉疚,“大殿下知道你我同出一门,希望我能借此拉近两方关系。我无意打扰你,但也不得不送些信物来。”
“那为何不留一两句话,我险些以为……”
“你若因此以为我存心要利用你,从此再不愿见我,那才是最好的。”宣存礼苦笑,“师兄一身都是祸端,不要沾惹到你身上。”
“明明早就想好了若你还是愿意见我,那我该说什么才能让你觉得痛楚,再不想见我。”洗旧白的旧衣袍被风吹得贴在身上,本就瘦削的身体显得越伶仃支离,再不见昔日风姿意气,“可真见了你,又不忍说那些话让你伤心了。”
宣存礼想起方才书房里那盘棋,白子落棋全然是裴煦风格。他爱吃樱桃,那位殿下就连书房这种地方都随处备着,棋只下了一半,兴许他来之前两人正在对弈,他们感情应当很是不错。
“你从前日子过得艰难,现在苦尽甘来已是不易……师兄现在满身泥泞,你不要近身。”
裴煦想不出他这几年是如何过的,竟把自己耗成这样。他想上前几步好好问问,宣存礼却像受了惊吓般连连后退。
“止步,止步,不要上前来了。”那双眼睛哀戚,几乎要落泪,“若你想要我好过一点,就不要再上前来了,昔日里和我有旧的人,只剩下你了。有时我也开始信命,是不是自己克了他们……若你今日近我,来日出了什么事,我万死也难辞其咎。”
裴煦因为他的抗拒而显得手足无措,呆立在原地看着他离开。
姬元徽站在不远处看着,觉得裴煦的表情看起来快被冻僵了。他走上前去,将茫然站在那里伤心的人拉到自己怀里暖着:“你想帮他?”
裴煦张了张口,垂眸摇头:“可他不用。”
“真可怜。”姬元徽的语气听不出喜怒,手搂在他腰间拥着他往回走,“你的好心又被人回绝了。”
进门后,姬元徽倒了杯暖手的茶塞到裴煦手中。
大概是因为今天见到的人和记忆中那个意气风的师兄相去太远,裴煦显得有些恍惚难以置信。
那人在他的记忆里太过聪明俊秀,无论什么事应对起来都游刃有余,所以他下意识里就觉得,只要他活着,无论在哪里都有能力活得很好。
可人的心一旦被捅碎了,又怎么可能还有心力去在乎自己过得好不好?
“世事难测,就连我也听说过你那位师兄昔年颇有美名。”姬元徽道,“而如今若不是你说他就是那位宣公子,恐怕已经无人能认出他们是同一个人了。”
“宣氏与当时的大理寺卿陆氏是世交,师兄与陆家独子情谊深厚,原本连婚期都定下了……”裴煦捧着茶盏的手指收紧,“可太子觊觎我师兄才德容貌,横插一脚,一定要宣氏悔婚将师兄送到他府上。”
“师兄不愿,宣大人也不同意……不久后宣大人被丞相请去闲叙。”裴煦长长呼出口气,“后来生的,就是从三品大员国子祭酒宣大人被人当街杀害,大理寺卿陆大人为其鸣不平,也被株连下狱,从此宣氏陆氏败落……”
一切的一切,全都是挟私报复。
“父母亲人,还有未婚夫,全因太子一己私欲遭难。”裴煦将茶盏放下,垂眸:“这大概也是他愿意去投大皇子的原因。”
实在是很惨烈的过往。
姬元徽停顿了下,然后将方才宣存礼留下的契券递给裴煦看:“科举一事,事关国本,无论如何都是要查的,但这事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也和太子扯上了关系。”
裴煦将那张纸票接过,放在手中翻看:“科举是国本,太子也是国本,殿下是担心陛下会舍前者保后者吗?”
姬元徽眉头一动:“不会吗?”
“殿下多虑了,至少现在陛下还不必做取舍。”裴煦温声道:“从来都没有昏庸的储君,只有不尽责的师长和邪佞的属官。”
姬元徽抬眼,思路明朗了许多:“你的意思是,这次无论如何,被处理的都只会是丞相?”
“这是好事,毕竟若是根系不铲,无论枝干如何被摧折都还会有复萌的机会,而王家就是太子党的根。”裴煦微微笑起来,“陛下虽说离京养病,但也不可能半点都不知晓京中消息。今日情景,陛下不像不知,倒像是顺势而为。”
[陛下恐怕已经有意要废太子了,但因为做的比较彻底而有些慢,王胤若倒了,太子党再想复起就难了。]
[届时哪里还有什么天潢贵胄呢……只剩丧家之犬,任人打杀。]
后面两句语气太像乱臣贼子,裴煦大概是还顾及着那么一点读书人的体面,点到为止,没有直接说出口,而是微笑着抿了口茶,心情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
他眼睛里有光,宁静而平和,但若是细看,温柔的神情下虚虚掩着的却是涌动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