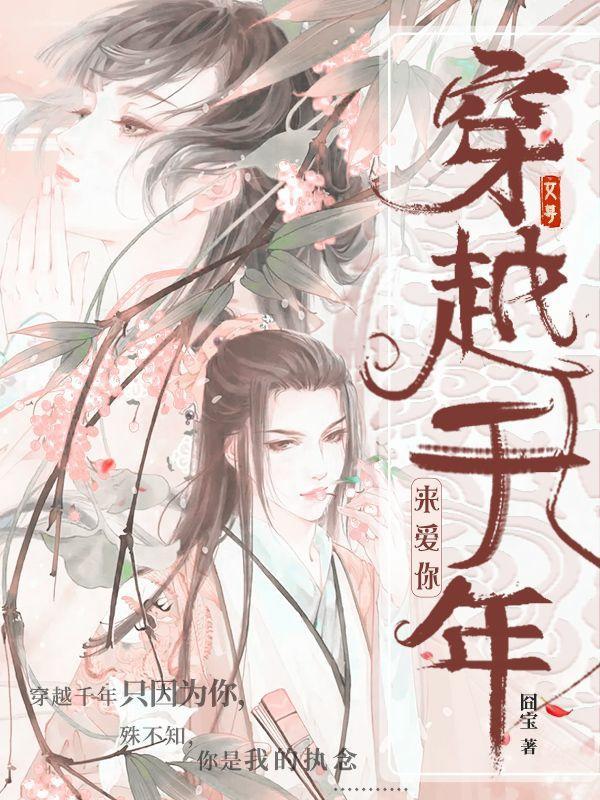笔趣小说>献给东宫后 故砚殊 > 第50章(第1页)
第50章(第1页)
闻人恪冰冷的目光从她身上扫过,语气幽森:“孤以为,母后告诫过你,不要在孤面前随意开口。”
香织瞬间噤了声,因为她确实想起来,很久以前有次皇后娘娘确实叮嘱过她们,遇到太子说话不论他说什么,只管顺着太子的意便是。只是这么多年她们与太子殿下打交道的次数太少,大多时候也都有皇后娘娘在场,轮不到她们说话,渐渐也就忘了娘娘的嘱咐。
冷意立时浸透了香织的骨髓,一种死亡笼罩的阴影仿佛当头罩下。
闻人恪这忽然的变脸也让阿洛狠狠惊了一下,虽然她也着实经历过几回太子殿下的阴晴不定,却从来没有哪一回像此刻般令她确信他真的动了杀心。
或者说,此时此刻,在太子眼里,香织已然是个将死之人。
“殿下……”阿洛迟疑地唤了他一声。
闻人恪转过身来,眉宇间依然残余几分未曾消散的狠戾,但比起方才,已然算得上温和。
“坤德殿离得不远,走吧。”
说是不远,可到底还是隔了几座宫殿的距离,好在林钟不知从哪抬了一顶小轿来,倒也没真的让阿洛自己用脚走过去。
那厢苏皇后正在大殿与一众命妇夫人们叙话,就听到宫人通禀太子殿下携了侍妾一道来给她请安。
苏皇后动作一顿,掩下眸中一闪而过的惊诧,半真半假地笑嗔道:“亏他还记得本宫,这都多少日子没来给本宫请安了。”
说笑间,闻人恪踏进殿门,闻言接道:“母后这话可真让儿臣惭愧,今儿就是来给母后赔罪的。”
太子进门,在场的夫人小姐纷纷起身行礼,动作间不免朝殿门方向看去,只一眼就被太子殿下身后的人吸引了视线。
维夏扶着阿洛跟在闻人恪身后,因是要面见皇后,所以略微妆点了一番。
一袭月青色流彩暗纹丝绣宫装,衬得身形窈窕有致,头上挽了流云髻,鸦青的发丝垂在纤腰间,斜簪一支碧玉缠枝钗,耳垂挂一对同色翡翠滴珠耳坠,肤白胜雪,樱唇凤眼,清冷的色调完全压不住盈盈艳色,反倒更添几分似清还媚的撩人意韵。
直把一众内宅掌家的夫人看得忍不住暗自皱眉。
这样妖媚的女人,若不是藏在宫里,外头该有多少男人把持不住?
苏皇后亦是头一次见阿洛,十分意外地暗中瞥了眼太子,她确实没有料到竟是这样一个人得了太子的青眼。
该说太子这样的性子居然也没能过得了美人关吗?
阿洛神情自若地踏进门,对苏皇后盈盈一拜:“妾身参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那些夫人们的眼神她并不陌生,早在苏家的时候她便知道二夫人不喜她,除了因为她占了四姑娘的位置,还因为她的容貌。
同样在她还顶着苏四姑娘的名头时,也已明里暗里听过不少与苏家有交情的人家掌事主母暗示二夫人,以她这样的相貌,将来亲事只怕有波折。而这波折,也不过是个委婉的说辞。
苏皇后早已敛了情绪,笑着抬了抬手:“快起来吧。”
说罢,又转向太子道:“本宫也是听说巡狩一行你居然破天荒带了人,这才忍不住想把人叫来瞧瞧,倒是没想到你连这一会儿都舍不得,也要跟着来。”
阿洛起了身,乖巧地站到闻人恪身边。
听了皇后娘娘的话,只觉这深宫内苑也不容易,母子俩说话都拐弯抹角的。
闻人恪微微勾唇,话里听不出喜怒:“这就是母后误会了,儿臣只是恰好在宫里,听说母后召见,还以为母后是想儿臣了,正巧这丫头在围场的时候伤了脚,索性捎她一程。”
苏皇后当然不信他的话,只是嘴里顺着说:“既然伤了脚,你遣个人来说一声不就得了,还值得把人也折腾来。”
如此一说,倒显得是太子多此一举了。
闻人恪淡笑:“这不是您那位传话的大宫女直说苏家二夫人想念女儿想得不得了,您又最看不得人难过,这才让她务必把人请来么?”
一句话登时让苏皇后面上的笑意浅了,看向闻人恪的目光染了几分冷意。
不是她的错觉,太子今日确实是有意与她作对。
往日他们母子虽不和,但当着外人的面总还会做几分母慈子孝的掩饰,例如方才的对话,她分明已退让了,只要他跟着说一句孝顺她之类的话便能自然而然揭过,这样的操作两人从前都是驾轻就熟。
然而他偏不。
不仅不圆场,甚至还故意把她派香织去请人的事摆在台面上,一个“务必”足以令场面变得异样起来。
阿洛同样察觉到太子殿下的情绪似乎有些不对,转念想起他今日好像确实比之前回宫要早得多,不然也不会正好撞上这件事。
难道,是在宫外发生了什么事吗?
苏皇后紧盯着闻人恪,却丝毫不能从他的表情里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慢慢叹一口气,示弱般地道:“本宫就知道,一定是香织说话哪里说得不对,惹着你了,你这是来给本宫上眼药来了。得,本宫明白了,以后定然不会再叫她出现在你面前,行了吗?”
殿内,立在一侧的香织听见苏皇后这话,本就惨白的脸色瞬间蒙上一层灰败,沉到谷底的心被寒冰封住,整个人都失去了生机。
她明白,皇后娘娘嘴里的不再出现不是让她以后避开太子殿下,而是永绝后患的不再出现。
求生的本能使香织还想张口说点什么,但一瞬迎上苏皇后那双彻寒的深眸,凝聚的勇气立时消散,就连颤抖的力气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