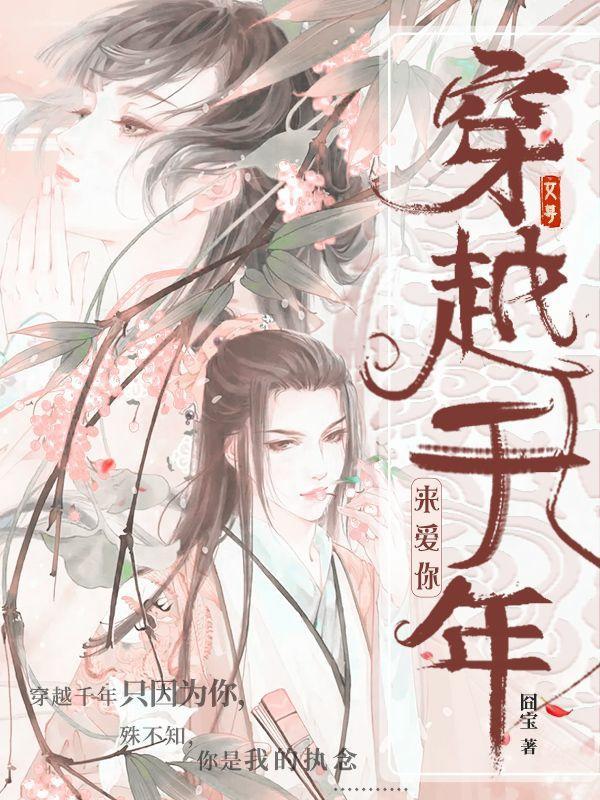笔趣小说>世子今天病好了吗全文免费费 > 第59章(第1页)
第59章(第1页)
皇帝坐在坐塌的另一侧,他脸色阴沉的盯着跪拜在殿中的如嫔斥道。
“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收买宫人,叫他在皇姐所乘小舟的舟头泼了油,到时你哥哥带着皇姐一同坠了湖,如此这般,皇姐不想嫁也只能嫁给这孽畜了是不是?!”
闻妙安听不见自是不知晓他们说了什么,便瞧着夏雨在那头比划给她看。
如嫔不曾想平日里算得上温情总是笑意盈盈的皇帝竟会为了此事生了这般大的火,她也是吓着了哆哆嗦嗦的跪拜在那儿说道。
“臣妾臣妾的兄长爱慕殿下多年,且臣妾的兄长也是容色品行皆佳,又无红颜知己风流韵事,现下又在朝中为陛下效力,若是若是殿下肯嫁于兄长,也是美事一桩啊兄长定会待殿下好的,陛下。”
这满殿的人听着都觉着这如嫔怕不是疯魔了,不然哪儿来的胆子敢给长宁殿下拉郎配?
奈何这如嫔竟越说越有底气的又道。
“陛下,今日之事是臣妾算计了殿下,但这算计也不是为了殿下的婚事?这晋北上下想成为驸马的人何其多,但不是个个都如同臣妾的兄长这般好的,殿下觉着呢。”
她说着竟瞧向了闻妙安,她想着刚刚她撮合这兄长与长宁殿下同游时,她神色上并无半分不悦。
反正事未成,兴许这长宁殿下能帮她说几句话。
只是闻妙安平生最厌恶有人将这算计打到她的头上,她未说些什么更未比划些什么,只是坐在那儿瞧着她。
瞧久了,如嫔竟蓦地生出些凉意来,她浑身一哆嗦就跪拜在皇帝的脚下。
皇帝倒是被她这一番言论气笑了,倘若这如嫔是个有脑子的是断然说不出这番话的,她既是个没脑子的,那他说那么多又有何用。
“母后,朕瞧着这如嫔胆大包天竟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谋害皇姐,既如此便褫夺封号打入冷宫,至于乔行简竟妄图毁了皇姐的清白便剥了他这身官皮,此生不得再入朝为官,母后以为如何?”
太后捻着手中的那一串佛珠瞧着那如嫔欲要爬过来求饶的模样便烦躁的紧皱着眉说道。
“依哀家看,这工部侍郎不会管教儿女,既如此他这工部侍郎也不必当了,至于降为什么,陛下看着办便好。”
这如嫔本想借长宁殿下招驸马一事带着乔家再往上爬一爬的,如今她大梦落了空,又被打入了冷宫,自是难以接受的欲要抓着太后娘娘同皇帝的衣摆求情。
只是还未等她凑上前去,夏雨便吩咐着小太监将这如嫔拿下,后而直接拖了出去,至于那乔行简自也是如此的。
待到这两个祸害出了含章殿,那皇后便带着身侧的德嫔也跪拜了殿中请罪道。
“母后,今日之事臣妾也有罪过,是臣妾执掌后宫不力,才出了此腌臜事儿,是臣妾的错。”
待到皇后话落,德嫔便也说道。
“臣妾也有错,臣妾平日里随在皇后娘娘身边儿,帮着娘娘协理六宫,却出了这般难堪的事儿,还望陛下,太后娘娘,长宁殿下责罚。”
这二人一唱一和的请了罪,倒是聪明。
今日既出了此事,那她们二人必定难辞其咎,与其等着皇帝同太后问罪,不如早早地请了罪,也好了结了此事。
太后自是会借这此事好生敲打敲打这后宫的风气,她将手中的佛珠放在一侧的小桌上说道。
“那便罚半年的月例银子以儆效尤罢,若是日后再生此事,便不会只是罚银子就能了结得了。”
到底是要给这新后一些脸面,今儿若是重罚了她,那她日后又哪儿来的威仪执掌后宫?
“谢娘娘。”
皇后同德嫔双手交叠在额前深深一拜,皇帝瞧着便也说道。
“行了,你们今儿也回宫罢,不必待在含章殿了。”
“是。”
如此,此事才算是有了个了结。
只是这有罪之人都受了罚,那有功之人在何处?
“那赫连氏的小子呢?带来吧。”
太后知晓闻妙安刚刚将那赫连嵘辰安置在了西偏殿,便也吩咐着夏雨去将这人请来。
今儿若不是赫连嵘辰,那妙安怕是真要嫁给那不堪之人了。
“是。”
夏雨领了命便欲要出殿去将那赫连世子爷寻来,奈何人还未出殿,便瞧见那赫连世子从那小厨房走了出来,他入殿便作了一揖道。
“草民给陛下,太后娘娘请安了。”
太后沉着的脸色稍缓,她轻叹一口气摆手免了这人的礼道。
“坐罢。”
玉簪本是将那圆椅放至在皇帝的坐塌下,奈何这赫连世子竟抬着那圆椅坐在了闻妙安的身侧,明颂雅在一旁瞧着也是唏嘘的轻“啧”了一声。
“今儿多亏了赫连世子,不知赫连世子想要个什么赏赐?”
赫连嵘辰听着太后所说之话便瞧向了身侧的闻妙安,他伸手去拽了拽她的衣袖。
闻妙安秀眉微皱的瞧了过来说道。
“想要什么就同母后说,只要不危害江山社稷,母后都会应了你,莫要扯本宫的衣袖。”
赫连嵘辰似是就在等着闻妙安的这句话,听罢他便起身作了一揖道。
“四日前,草民曾入宫给太后娘娘请过安,那日草民便是为着长宁殿下的驸马一事而来,今儿,既太后娘娘问了,长宁殿下又这般说了,那草民便想参选驸马大选。”
闻妙安瞧着玉簪所比划的便愣了一瞬,她想了许多这人会要些什么,却不曾想这赫连嵘辰打的是她的算盘。
可这人不是还费尽心思的想要登上族长之位?若是成了驸马可就要长长久久的留在京洲城的长宁公主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