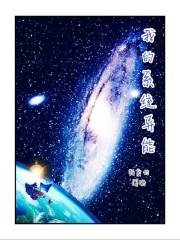笔趣小说>你好我来自怪物游戏 > 第34章(第1页)
第34章(第1页)
翠缥
看守所内的灯光煞白,致使空间上下割裂感极强,阴影像是沉淀,全部淤积在下层。
围栏隔开的许为次垂头不语,瘦弱的体格和落肩的头发让他越发女相。
“还以为你同意委托是想开了,这咬死牙关不打算说是在干什么?”
潘幼柏语气与以前一般无二,一身笔挺的西装,局外人似的履行着职责。
“劝你还是说说得好,我知道你抱着什么心态。”
许为次缓慢地抬头,在视线即将触及潘幼柏前又低了下去。
“你知道吗,疑罪从无,所以在担心自首坦白会给你减刑前,你最好担心一下案情不清会让你的愿景落空。”
许为次指尖一颤。
说话时,潘幼柏的笔尖在纸上画出一条力透纸背的斜线,收尾前笔锋颤抖,线条乱成了一团麻。
“你大可放心,律师没那么大的权能,不能在法庭上巧舌如簧便为犯人洗去罪孽、从轻判处,金牌律师也不例外。”
围栏投下的阴影一格一格印在纸上,潘幼柏便细细沿边描着,像小时候把课本上包口的文字涂黑似的,“一分罪一分罚,我们实际的作用只是让一分的罚不要变成两分,也不要变成半分。”
“我坚持程序正义,只是对我而言,那是走向结果正义’最宽‘的道路。若是不能保证公平,让无辜者含冤,让恶极者脱罪,那是权利的倾斜,也是我们的无能和失职。”
潘幼柏欺身,白色的光带落到脸庞上,眼中晦暗不明,“该你死的你说不说都得死,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增加别人的工作量。”
话至此,许为次也终于开了口。
他能从潘幼柏眼里看到浓烈的恨意,一种被平静裹挟住的暗潮汹涌。
那份平静让许为次首次感受到,有的人真的与众不同:不因感情影响判断;不因私事混乱公务;不因情绪阻断逻辑。
几日后的法庭上。
面对公诉人拿出的证据,潘幼柏一一质证,“关于证据三,死者伤口呈撕裂状,齿痕清晰,但尺寸过大,与人齿明显不吻合……”
潘以凝左侧肩颈有一处巨大的伤口,伤及颈动脉,失血过多是明确死因。
法医鉴定结果是撕咬伤,给出的凶器预设是类似于大型猫科动物的牙齿,例如狮子。
痕迹明晰,没有类似于凶器来回进入和用力不够的情况,也就是说咬合的力度很强,绝不是人类可以不借助外力达到的水平。
在凶器尚未找到的情况下不好判断杀人手法,单凭许为次本人的石膏模型一说难以成立。
“而证据四,七里巷的监控覆盖范围不够,仅有的监控记录中有拍到死者潘以凝的身影,但一次都没有拍到被告许为次,缺乏犯案经过,甚至无法拼凑出前因后果。”
调查过程中,警方在七里巷发现了一处租住房,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房屋破败,所以租金便宜,手续也是粗略带过,以至于查到这花了很多时间。
但是能够确定租住人是潘以凝和许为次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