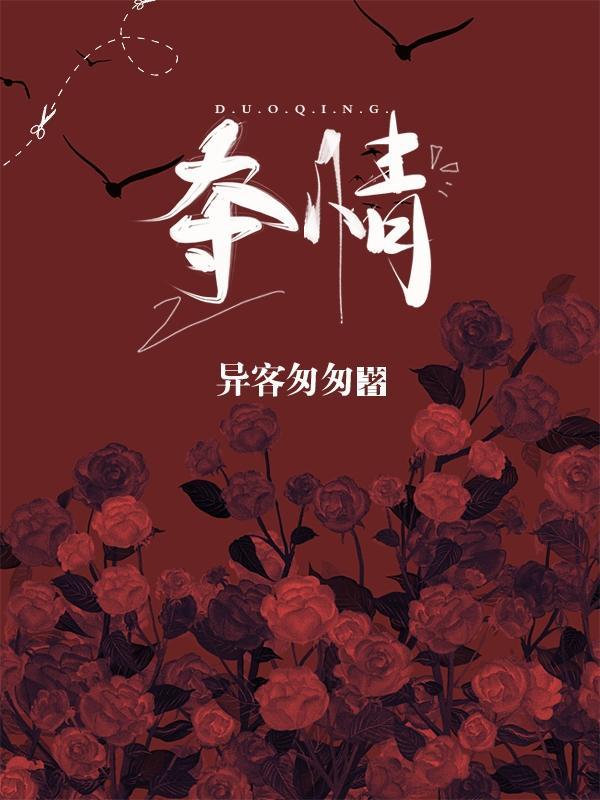笔趣小说>渣了前世恋人后[穿书 > 第88章(第1页)
第88章(第1页)
台上的人言笑晏晏,周围的人也跟着起哄。台上的小厮侍女都退了下去,检场的放了一个屏风,便?示意是洞房之中。小生起来?略讲了几句对白,然后?便?拿起喜称,缓缓地挑起了新娘的盖头。盖头下一张明媚惊艳的脸庞,满目的柔光都投射在那一人身上,台下纷纷杂杂,可方竹的眼中就只有白元觉一人,她是真?心?的,不是做戏,把自己的全身心?都交给了白元觉。
台下有人道:“哇,这演技也太好了吧,这哪里是在做戏,我觉得这小生和花旦就是在成亲了!”
有认识的人道:“他们俩听?说就是一对夫妻啊,只是有名无实。”
“哎,道听?途说不可信,眼见才为实,你看?如今两人的眼神分明不是在做戏了,就当他们重新又成了一次亲。成亲哪有不哭的,这新娘子笑的可不像演的。?”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句有名无实,傅意怜自责自己沉浸在个人的哀痛中,竟无视了身边人的挣扎。重来?一次,只是她补偿给方竹的这个婚礼又真?的是她的解药吗,她知道这是戏吗?
“阿南,你说,我们最担心?的事情,会不会发?生?”
荣山南冷眼旁观下属将?一众乱贼分批看?押,淡然道:“你是说,方竹会再次对老四一往情深,不可自拔?”
“是啊,你觉得不会吗?”
还没有听?到答案,余鸿鉴再也按捺不住,什么公子体面,修身涵养,都统统滚到一边。他恨恨将?酒杯摔在地上,外面的人一听?,摔杯为号,立即攻入城中。
美梦忽地被打碎,荣山南抽出压在大氅下的宝剑立刻与?人拼杀起来?,余鸿鉴快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待人攻入了那地下的暗牢当中。所有失踪的少女都在里面,他们正在进行着一种仪式,马上就要将?那少女生吞活剥。余鸿鉴立刻派人麻利地将?他们救了出来?,这一场仗可算是非常成功,将?他们一锅端。
余鸿鉴因此大受表彰,可这份表彰可以说是给自己加冕。裴都督早已无干政事,这宛州城的首领,早就是他余鸿鉴了。
此事过去几天之后?,善后?的所有工作才全部完成。荣山南趁此在平州部了军,余鸿鉴却无法反驳。
傅意怜这些?日子也时常能听到裴雁知的故事,他们说她病得瘦脱了相,这场比赛万万没有想?到会搭进她的二哥,而且他们是赌上了极严重的一批货,不仅跑了许多货商,如今已经入不敷出,极为艰难。可也有人说,他们树大根深,就算是没有了这些?庄户,不是还有都督庇护他们吗?
一人说道:“这你就不懂了,如今都督都倒台了,还有谁能护着他们呀。”
“再说裴雁知的父亲贪污受贿,已经被余鸿鉴给查处了。”
“什么?余鸿鉴也是他的女婿,怎么能这么狠呢?”
“唉,早就听?说他要跟裴雁知和离,一直没成,不知道是不是要旁敲侧击啊。”
傅意怜知道,这些?说不定都是做给她看?的。当然,也可能不是,她不认为自己在余鸿鉴心?中有那么多的分量。就好比说,今日余暄妍来?闹的这一场。
自从被赶出了傅家,余暄妍就一病不起。傅淮安初初倒是时常去看?她,日子久了,去的次数也少了。他是不敢搬出傅家的,毕竟除了这里,他也没地方住。
余暄妍寒了心?,一开始拼力要傅意怜吃亏,后?来?在病榻上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一个被她欺负得垂头丧气,去的去,散的散。
尤其是哥哥,白莲教的事,她向来?是支持的。怎知傅意怜横插一杠子。余暄妍拼尽一口气,叫来?夏莲,气若游丝问道:“夏莲,你是不是我的好奴婢?”
饶是这般时候,夏莲也是描眉画腮,绫罗绸缎样样不缺,半蹲在床边答道:“主子,您是奴才永远的主子,不管您去哪儿,我都会跟着您的。”
余暄妍道:“是吗?果真?跟着我,那么为什么开始变卖府中的珍奇古玩,你收集的那些?钱是不是想?要半途上回去过你的逍遥日子?”
夏莲心?里一惊,险些?跌落在地:“主子,奴婢没有啊。”
“没有?你以为我病昏了头,便?不知你做的那些?事?我待你不薄,如今你却要弃我而去。”夏莲心?知躲不过,嘀咕片刻,横竖如今屋子里再无旁人,破罐破摔道:“主子您以前也说过,想?要给奴婢找一个好归宿的。”
“好归宿,是好归宿。”余暄妍如今不禁想?起秋歌。秋歌在余府上住了那么多时日,动辄打骂,傅意怜一回来?不还跟着她的旧主去了,她所承受的那些?屈辱不过都是为了她的主子,为什么夏莲就做不到呢?
事到如今,余暄妍不禁想?起一句话:仆随其主,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仆人,她看?着夏莲这幅过河拆桥的恶心?模样,不由得想?到自身,难道在别人的眼中,在傅淮安、裴雁知的眼中,她就是这么一副令人恶心?的模样吗?余暄妍撑着身子坐起来?:“我也不怪你,如今你要走,我可以放你去个好归宿。不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会连梳洗打扮都不愿意给我做吧?”
夏莲一听?有底,连忙道:“奴婢不敢。”
她替余暄妍选了一身鹅黄襦裙,替她梳了一个极为精神的倭堕髻,插上她最喜欢的玉簪,这才问道:“主子,咱们如今要到哪里去呀?”
余暄妍道:“去傅意怜家,给她赔罪,看?她是不是能放过我们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