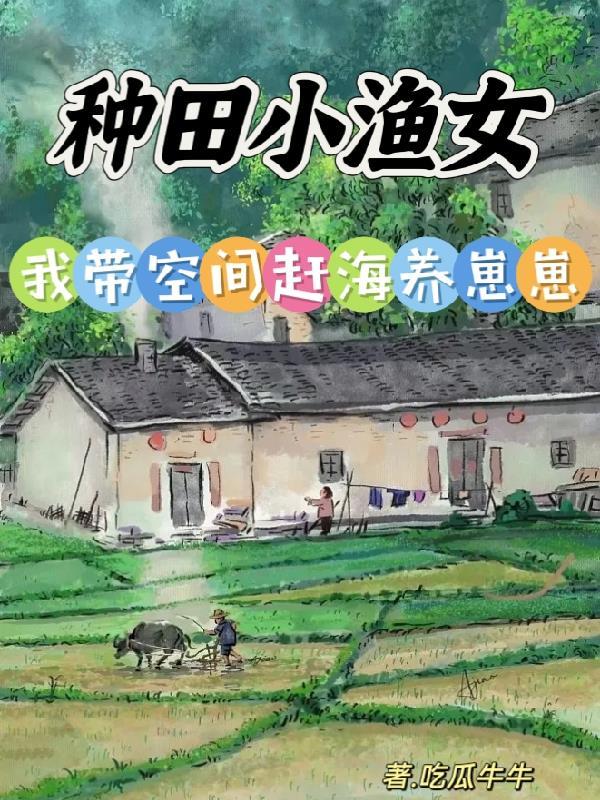笔趣小说>还璧 靡宝 > 第60节(第1页)
第60节(第1页)
这是宋绮年金盆洗手后过的第二个年。宋家的亲戚们都远在外地老家,同宋绮年他们这一房来往不多。这个年,显然只是她们娘儿三个一起过。
过去在千影门里,过年是一个极其隆重的活动。不光所有门徒齐聚一堂,还会有各种祭祀、宴会和论功行赏的活动。
只是在那个人人彼此倾轧斗争的环境里,宋绮年从没感觉到家的味道,年自然也过不伦不类。
而如今,光是看着柳姨絮絮念着菜单,看四秀从炭盆里扒拉出烤好的红薯,宋绮年便被这温馨平静的生活而感动。
门铃在这样的雨夜显得十分突兀,但宋绮年并不意外。
“我去开门。”
宋绮年披上大衣,穿过已熄了灯的厅堂,打开了大门。
傅承勖果真站在门外。
雨有些大,他又没有打伞。从巷子口走过来这短短一段路,他的帽檐、肩上都已湿了一片。
幽暗的光线中,男人宽厚的肩背几乎将屋檐下的灯光全部挡住,把宋绮年笼罩在阴影里。他低头望着宋绮年,目光柔顺且谦恭。
“我是来正式向你道歉的。”
水滴自傅承勖的帽檐滚落在他的衣襟上,在上好的精纺羊驼绒面料上留下一串水迹。
宋绮年后退了一步:“请进吧。”
傅承勖并非空着手来的,他手里还提着一个用防水油纸包着的方盒子,看样子还不轻。
客厅里的火盆已经撤了,屋子里冷得很。
“如果不介意的话,请去我的工作间坐坐吧。”宋绮年道。
凌乱的工作间里,傅承勖不用旁人招待,自已提来一张凳子,坐在工作台边。
宋绮年继续给一条晚礼服钉着珠片。
傅承勖注视着女子姣好又安详的侧脸,看灯光在她浓长的睫毛下投下一片阴影,看她因为专注而不自觉轻轻抿着的唇。
雨声淅淅沥沥,衬得小小的工作间里更加温暖安详。暖意驱散了傅承勖身上的湿冷水气,又因炭盆里烤过红薯,空气里还残留着一股甜香。
“我……”傅承勖极罕见地踯躅着,斟酌着,道,“我出生的家庭虽然非常富裕,但在我童年时便突然败落。我失去了双亲,很是吃过一点苦。这段经历让我变得非常渴望强大,迷恋权势——唯有手握强权,才不会落入任人欺凌的地步。可这又确实让我从受害者成为一个施暴者……”
宋绮年没想到傅承勖会这么直白地剖析自已。
这种检讨,以她的傲气都做不到,更何况傅承勖的傲慢比宋绮年只多不少。
“在这之前我从未为此反省过。”傅承勖坦诚道,“当你拥有了庞大的权力,你很难不去利用它来让自已的生活更顺心如意。而且操纵他人是一件会上瘾的事。掌控别人的命运会让你觉得自已更加强大,好像一个神……渐渐地,我有些得意忘形。直到我遇到了你……”
宋绮年没有抬头,但手上的动作慢了下来。
“老实说,你是第一个因为这种事对我生气的人,也是第一个点醒我的人。你完全有权力生气。这件事是我做错了。我不是说以后我就不去弄权——这世道,胜利属于强者,我依旧会手腕强硬,有必要时不留情面,甚至有可能不择手段——但是……”
傅承勖注视着宋绮年,目光如月光下的海洋:“你是我的搭档,是同伴,我不应该那么对你。”
宋绮年终于放下了手里的活,朝那个男人望去。她清亮的眼眸则像山间的幽潭。
“我保证以后会以真诚、平等、尊敬的态度对待你,宋小姐。”傅承勖郑重承诺,“我也会以全新的角度去看待和尊重他人。我也许还会犯一些大男子主义的错误,希望你能指出来。”
他顿了顿,最后道:“宋小姐,我并不完美,但我愿意去改正。”
宋绮年又垂下了眼帘。
就这样吧。各退一步,海阔天空。
高傲自负如傅承勖,做到这一步已出乎宋绮年的意料。再僵持下去,傅承勖抽身走人,宋绮年只会得不偿失。
“这天下没有完美的人。”宋绮年低声道,“我也有一堆毛病。我们都在努力把自已变得更好罢了。”
这话说得很是圆滑漂亮。
傅承勖眉宇舒展,一股厚重的温柔散发了出来。
“所以,宋小姐,”他身子稍微前倾,目光专注,“你愿意和我恢复合作吗?”
宋绮年觉得自已应该更正一个看法:如果你觉得一个强大坚毅的男人展现出无奈忧伤是最震撼的一幕,那你该看看他对你露出讨好的表情。
“为什么是我?”宋绮年问,“傅先生没有去找过别的贼,还是没有找到比我更合适的人?”
“我从来都没有考虑去找别人。”傅承勖道。
“为什么?就因为我是偷走这批古董的人?”
“这是原因之一。至于其他的理由,等到时间合适了,我会告诉你的。”傅承勖又想起一件事,“哦,对了,那个铺子,我想以零租金的方式把铺子租给你——”
他抬手示意宋绮年先不要说话。
“——我会在你未来三年的收入里抽取一定比例的分红。我想做你生意上的合伙人,想和你一起打造一个服装帝国。就看宋小姐意下如何?”
这个合作方式很公平,也非常合宋绮年的心意。
见宋绮年露出明显的赞许之色,傅承勖又道:“还有,我今天过来,还给你带了一份赔罪的礼物。”
他把那个礼物盒子递了过来。宋绮年撕开了牛皮纸,发现里面是四张装裱在金属相框里的画。
那不是普通的画,而是……
“这是一套阿尔丰斯·穆夏的《四季》。”傅承勖道,“是1900年在巴黎世博会上发布的丝绸版。瞧这里——”
他指着版画下方某处:“这里有穆夏基金会的印章,版画的编号,巴黎世博会的标记,还有制版师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