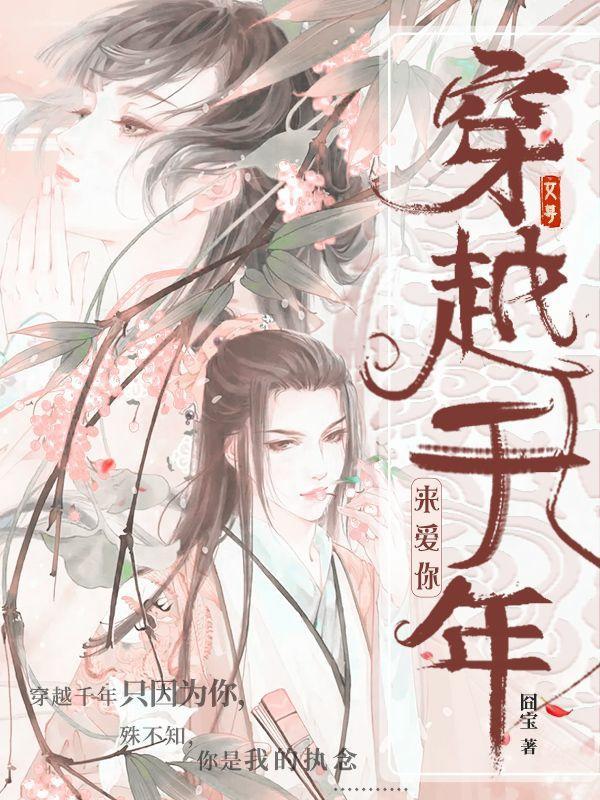笔趣小说>涨红的意思 > 第60节(第1页)
第60节(第1页)
“为了你呀。”
“说谎,”叶洗砚的酒窝并未如千岱兰的预料出现,他说,“你是为了你的服装店。”
千岱兰的大脑卡了一下。
“……你该回学校好好读书,”叶洗砚克制着声音,他说,“也没关系,现在才十月份,还来得及;服装店不该占用你太多时间,你可以雇佣员工,还有你的父母——”
“我已经雇了人,”千岱兰打断他,“是我们附近大学的学生,但是她还需要学习——”
“你呢?”叶洗砚难得打断她,“你打算什么时候学习?”
千岱兰说:“店里没人的时候,我其实都在学……”
“你发给我的成绩单是真的么?”叶洗砚盯着千岱兰,问,“你和我说,你在学校里上课,测验;实际上,你在哪里做的那些题目?”
千岱兰哑口无言。
她不能反驳,也反驳不了什么。
她其实没想到今天的叶洗砚会这样直接地戳穿她的谎言。
千岱兰以为对方会像之前那样,看透她的谎言和小把戏,也继续心领神会地陪她继续演下去。
这次为什么不一样了?
他不是很喜欢这种扮演么?
现在的叶洗砚看起来似乎很生气,但千岱兰弄不太清楚他生气的点。
她尝试去理解,放缓声音:“我不是不想好好读书呀,但从高一读好像有点太慢了,现在老师讲的那些东西,我都自学过了……而且我还通过了会考,下一年就能参加高考。”
叶洗砚问:“你打算只用一年的时间来准备高考?”
“嗯呢,”千岱兰点头,“熙京不是也跳级了吗?他不是初中和高中都只读了两年就参加考试?他还和我说,他的高中从来都没有晚自习。”
“他一直都有私人家教,高中从没有晚自习是因为晚上要接受六个家教老师的专门指导,”叶洗砚说,这个时候提起叶熙京,令他有种恼怒的烦躁,“你呢?岱兰?你打算在开店的业余时间外花一年来冲击高考?”
千岱兰再一次卡住。
“别浪费自己的天赋,”叶洗砚深深看她,现在的他成功地压下那种无名火,尽量温和地与她沟通,“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说过的话么?你说你是清华的学生——以你的聪明才智,好好学习,考上清华有极大可能,我相信你的能力。”
千岱兰沉默了,她没说话,低头看自己的鞋子。
是从上一个酒店中拿走的一次性拖鞋,干净的白色无纺布,消过毒。
叶洗砚给她预订好的房间是个酒店套房,在84层,卫生间都要比她的这个小房间大,浴缸侧的落地窗能俯瞰深圳城景。
除了叶洗砚在北京家的那个卧室,千岱兰再没睡过那么大的床,大到她可以以自己为直径,张开胳膊双腿随意地转着圈儿画圆。
叶洗砚的生活如此轻松,如此奢侈,如此……与这里格格不入。
近二十八年都顺风顺水的人生,大约从未尝过贫穷困顿的滋味吧。
钱对他而言什么都不是。
只是个数字而已。
他不可能理解她对钱财的渴望。
没办法,人总是会对自己拥有的东西熟视无睹。
千岱兰努力地想,就像她,也不会觉得美貌是很稀缺的东西。
因为她足够漂亮。
因为叶洗砚足够有钱。
她早该意识到这一点,不是吗?
“跟我走吧,”叶洗砚向她伸出手,“就当这两天什么都没发生,你回去后好好读书,不必担心钱的事情——”
“为什么不必担心?”千岱兰抬起头,漆黑的眼睛看着他,“我有什么资格不去担心吗?”
叶洗砚微微一怔。
千岱兰的声音微微发颤:“你以为我不想好好地回学校读书吗?你以为我不愿意和同龄人一样读三年高中、去考心仪的大学吗?你以为我很喜欢因为学历被瞧不起、被奚落、被辞退吗?你以为我愿意自己的努力被人一笔抹除吗?”
——叶洗砚,你没有在15岁时经历过职校的校园霸凌,你没有在16岁时在深圳的电子厂中被3、40岁的猥琐老伯尾随过,你没有在17岁就经历被初恋朋友的羞辱,你没有在18岁就背井离乡、独自去北漂,没有在19岁时学会对所有人笑脸相迎,应付同事间的勾心斗角。
——叶洗砚,你没有经历过饥饿,没有连续一周都吃那种又冷又硬的便宜面包和馒头夹咸菜,没有
经历过吃到吐还强迫自己吃的痛苦;你没有经历过在学校食堂连打菜都舍不得、和朋友拼一份的窘迫。
——叶洗砚,你试过冬季只靠一件丝绵都结块的棉服过冬吗?你也会被同学捂着鼻子嘲笑说一件衣服穿一个冬天吗?你感受过唯一一件过冬棉服不小心被划破时的难过、窘迫和焦虑吗?
你都没有。
生下来就在北京的叶洗砚,知道她想留在北京需要付出多大的艰辛吗?
早看惯浮华喧嚣的叶洗砚,知道她为了触碰到那一点点的繁华边角需要多努力地去踮脚吗?
所以你以为“穷”只是一种状态。
你不知道“穷”也是一种心理疾病。
“我必须赚钱,”千岱兰说,她咬牙,看叶洗砚,眼神倔犟,“NoworNever,我不会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也不会让它从我眼前消失;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境地,无论什么东西——我可以舍弃其他所有东西。”
“岱兰,”叶洗砚沉沉,“你年龄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