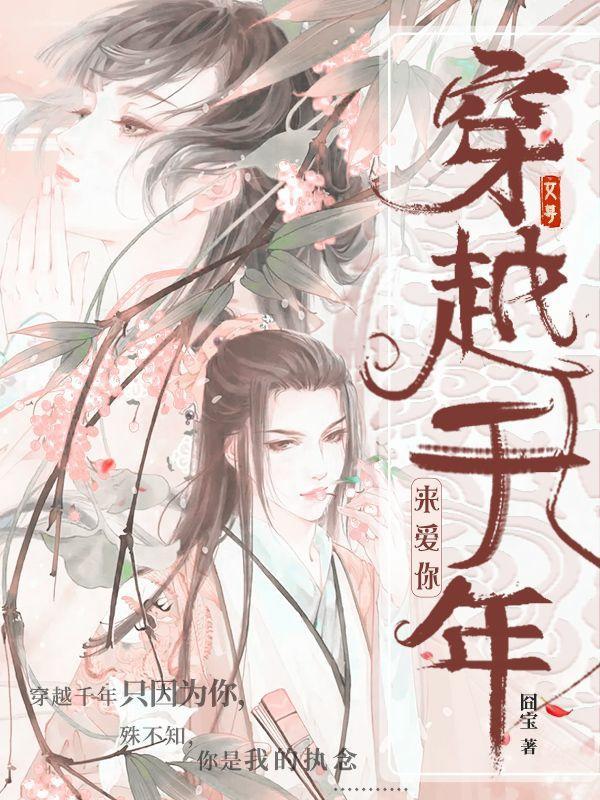笔趣小说>你知道将军 > 第2节(第2页)
第2节(第2页)
严管家一愣,没想到平日里任人拿捏的小少爷,居然敢明目张胆地指责自己。
他心中不快,但又不能在明面上顶撞花竹。当即双眼一转,对花竹说道:“我正是来履行职责的,今日让它偿了命,给您一个交代。”
花竹转过头来看他,严管家也不甘示弱,瞪着眼睛直视回去。
两人僵持了片刻,最后花竹冷眸微动,一抹笑容反而绕上嘴角,“它若死了,不过是出口气,丢了的东西仍旧回不来。”花竹指了指姜姜,“他生得可爱,也会捕鼠,让望舒带去集市上卖了,倒能帮你补些钱回来。”
管家泛着油腻红光的嘴一开一合,踌躇了半晌——他既不想遂花竹所愿,也不愿放弃一笔横财。
直到被随从提醒了一声,才道:“不劳花少爷费心,明日我亲自去卖。”说罢,又补充道:“您安心等出嫁就好。”
花竹没理会他的讥讽,和望舒一起看着姜姜。
一个小厮找来了竹笼,想把姜姜放进去。
姜姜不愿进竹笼,“啊呜啊呜”地叫着,管家看了主仆二人一眼,当头一棍朝姜姜打了下去。
姜姜没了声响。
花竹看着趴在竹笼里的猫咪,仿佛看到上一世的自己。
还有千千万万个驭灵人。
忍耐,花竹,忍耐。
花竹在袖子中,将一根根手指握回成拳,等到怒意压下去了几分,才示意望舒过来。
望舒没了平日里那股子活波,抽抽嗒嗒地走上前。
严管家让人拎着竹笼走远了。
花姨娘和常老爷仍旧站在檐下,不知道在商量着什么。
花竹见众人走远,递给望舒一小罐药膏,打发他去上药。
“少爷,姜姜怎么办?”望舒接了药,却不走,挨在花竹身边期期艾艾地问。
“你去擦药,剩下的我来。”
“姜姜可是我从厨房每日偷东西,才喂大……”
花竹看着门外的常老爷,朝望舒比了个噤声的手势。
望舒双手叉腰,在屋里走来绕去走了两三圈。直等到常老爷和花姨娘商议完毕,再次进了屋,才终于想起来自己身上的伤,揉揉屁股,拿起桌子上的小罐,嘶嘶哈哈地去了外室。
花竹目光平静地扫了两人一眼,他知道花常两家对于此事筹划已久,断不会如此善罢甘休,只等着看他们还有什么招式可用。
“跪下!”常老爷重拾最初的威严,一手紧攥衣角,一手指了指床前的地面。
花竹掀了下眼皮,依言下床,规规矩矩地跪了。
“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定贴虽不能再用,但毕竟是你父亲的遗愿,我亲自抄一份,送去常家。”常老爷看着花竹温顺的后颈,见他乖乖跪着,并不搭腔,逐渐胸有成竹。
花竹这孩子,性子温润,一向在他掌握的范围之中。
“你不要心气太高,常家的这位姑娘,已是能给你说上的最好亲事。你无父无母,虽然当了个小官,但也没有哪家高门大户的姑娘愿意和你成婚。”一想到自己既可以将花竹牢牢控制在手中,又可以受到本家的看重,常老爷心情十分舒畅。
“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下了。”
花姨娘顺势敲边鼓:“如此甚好,我这就去安排相亲。”
“慢着。”
花竹语调平稳又冷静,他仍旧跪着,甚至连头都没有抬起来,话说得也缓慢。
“印章还来。”花竹说得清清楚楚的四个字,落在屋子里,却是鸦雀无声。
他说的印章,是发给他个人的职官印。
当年他甫一上任,便得了两枚印章,这是其一。
另一枚是发给县尉司的官司印,他放在县衙,得以幸免。
而这职官印,当天就被常老爷要了去,美其名曰“反正你有另一枚可用,这印我先帮你保管,以防遗失”。
说白了,他怕花竹离开,以这枚官印来拿捏他。
花竹重生这半月以来,统共做了两件事。一是按照上一世的记忆,给自己找了一门协议婚姻,另外便是在找这方官印。
他偷偷去常老爷的房里翻找过几次,都无功而返。本以为是常老爷藏得好,但从方才管家的话里看来,常老爷大概是把这印弄丢了。
看来这院子里,想要拿捏人的,并不止常老爷一个。
常老爷听到花竹此刻要印,仿佛被窗外的雷劈到了,呆立半晌,没说出一个字。
花竹仍旧低着头,“那印是朝廷所颁,若是丢了,我被罢官,你要下狱。”
常老爷艰难地喘出两口气,嘴唇和下巴都跟着在颤抖。他收这印章的时候,一心想着以此控制花竹,却没成想,这印是一柄双刃剑,也有让自己流血的时候。
花姨娘却不知二人打的什么哑谜,扯了一把常老爷的袖子,催促道:“这亲事还订不订呀。”
听得“亲事”二字,常老爷复又振奋起来,目光里闪过一丝狂喜——只要花竹和常家成亲,那他和自己,便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永远蹦跶不脱。
他调整了一下表情,换上一幅和蔼可亲的面容。又将跪着的花竹扶起,让他在一张靠背椅上坐了。
“这常家小姐乃常家本家的嫡女′,你同她成亲,我们亲上加亲,同舟共济,没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