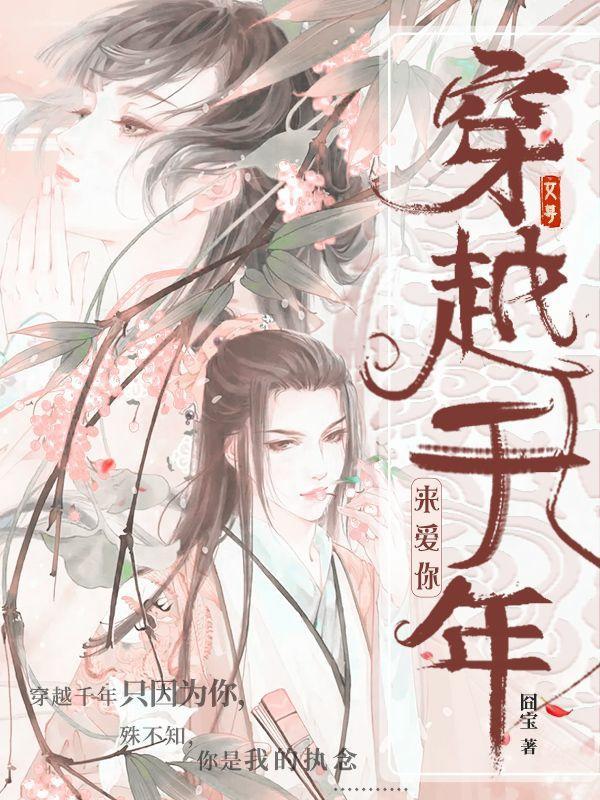笔趣小说>我住南墙全文阅读 > 第88章(第2页)
第88章(第2页)
只是这样的示好对于林缦而言是种负担。搁在三四年前,她是知道怎样应付的。心爱的人关心她、疼爱她,那就大大方方地张开双手,抱一抱、亲一亲,甜蜜回应。但如今,她只知道自己浑身上下的所有神经都在拒绝周贺南的靠近。
她不知道是什么让周贺南有了转变,更不敢往好的方面去妄想。
三天后,伤口拆线。
林缦像大部分成年人一样,忍痛能力一流,何况这又算不上伤。
只有周贺南把它当成大事,去医院接林缦的时候满脸焦虑,准备了一堆问题咨询医生。林缦看出医生的不耐烦,嫌他小题大做,直接将他从医生办公室拽了出来。
“你就不担心吗?”
“担心有用吗。”
没有用,谁都知道答案。谁也无法说到做到。
林缦在宽敞明亮的卫生间第一次打量额头这条疤。
光线直直地打在她的脑门上,与肤色泾渭分明的红、黄、青紫赫然在目。
真难看,难看到她从今往后看到“疤”这个字估计都会条件反射地心口发麻。
它就像一条扭曲的小蛇住在了林缦的额头上,蜿蜒攀爬,张扬挑衅。可即便恶心到了这个地步,林缦还是无法挪开眼睛。
她怔怔地几乎是将目光钉在了这条伤疤上。
为什么又是她。
明明她一直心怀美好,明明她一直拼搏奋斗,为什么她完全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比从前好过呢。
念书时,受制于父母的熏陶,林缦知道自家的贫穷是一种原罪,一种在社会各处都无法挺直脊梁的疾病。她什么都不太敢买,哪怕去买也只敢挑便宜货。然而事实上,她和方静姝一样,和全天下千千万万的少女一样,喜欢杂志里闪闪发亮的首饰和衣服。她也想弄一头又顺又翘的头发,露出一小截白皙脖颈,然后一个转头,将操场大半男生的爱慕收服。
但她知道,自己无法拥有那种人生,所以她埋头学习,毕业后又埋头工作。只是时过境迁,物质饱满起来,她的心却好像依旧空空如也。
香奈儿光滑的带着原始气味的丝滑羊皮没能抚平林缦额头的疤痕。
十几万一平的楼板更无法抑制悲伤蔓延。
林缦发现自己做不到无动于衷。
她的人生到底最缺什么。
像一只发条快速地拧紧。
透过门缝,流水响声不断。周贺南以为林缦忘了关洗手池的龙头,进去才发现抵在洗手池上的女人抿着唇,红着脸,两条泪痕清晰可见。
连哭都是隐忍不作声。
“怎么了?”他不自觉地皱了眉。印象中,林缦并不是一个爱美的女人,怎么区区一条疤痕就让她崩溃。他抽了两张纸巾,试图替她擦去眼泪。
林缦从镜中看见周贺南的动作,下意识地偏过头。
“没事。”她摊开掌心,用力地在脸上抹了一遍,泪水尽收,只有一副泛红的眼角无法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