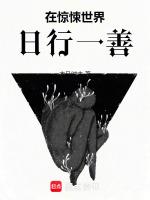笔趣小说>江山聘你全文免费阅读 >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五章(第1页)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五章(第1页)
這一行玄武軍將巷子附近的人家幾乎全搜了個遍,沒有找到姜嬈,眼下,只剩下最後一戶人家還沒搜了。
為的玄武軍帶人直接破門而入,簡陋的木門轟然被推開。勁風揚起一地的塵灰,在門外直射而入的天光下被照得纖毫畢露。
「咳咳!」當衝進門的幾個玄武軍被這塵灰嗆得咳嗽起來,他們身後領頭那人這才問話,「你們有沒有看到一個女子跑進巷子裡來!」
一邊問,也不等屋裡的人答,只將面前方才咳嗽的幾個玄武軍往前一推,直接下令道:「給老子搜!」
「官爺,這是幹啥啊!官爺!」眼見玄武軍到處亂翻,礙手腳的物件全被拂亂一片,屋裡的男人急得大喊,「官爺!我們可沒犯事啊!」
這屋子裡的住戶是一家三口,除了這喊叫的、長得一臉敦厚的男人,躲在男人身後的還有他的妻子,是個容貌平平、模樣生得和善的女子。而女子的懷裡還抱著一個嬰孩,瞧著不過五六個月大,屋子裡這麼大的響動,他竟還睡得酣甜。
這戶人家不算窮,玄武軍搜完了外兩間,還有一個裡間沒有搜。
領頭的使了個眼色,手下一臉兇惡地點了下頭,依令就要進去。
「官爺!」男人慌了,「這屋子不能進!這屋子裡睡得是我媳婦兒的三嬸子,她三嬸子患了——」
等玄武軍走得遠了,女人的哭聲驀地歇了下來。
領頭人退到了最安全的地方:「怎麼樣?」
她進了巷子剛發現無路可走,這戶的女人抱著孩子出門恰好看見了她,直接將她拉進了屋子裡來。
那可是能傳人的!
其餘的人也有些慌了,誰都不想染上這病。
「啊!這他娘的……這長得什麼東西!真他娘噁心!」
掀開被子,只見躺在榻上的人果然是個婦人,依稀可見臉上生了許多皺紋,但年歲卻因為滿臉的疹子和膿包看不出了。
「你,去檢查檢查床底下。」領頭人指了個玄武軍過去。
「滾開!」玄武軍一腳將人踢開,男人越是阻攔,他們越是覺得這屋子裡有鬼。
到了榻前,他不由分說地掀開了被子——
「砰」的一聲,玄武軍推開了裡間的門,入目果然看見榻上躺著一個人。
為的玄武軍早被榻上的情形驚得後退數步,他認出來了,那婦人臉上的疹子好像是麻疹。
「沒人,沒找到人。」
「你,還有你,進去看看。」領頭人發話。
他飛快檢查了一遍,出來的時候幾乎是跑著的,其他人怕被他挨著,紛紛後退。
「三嬸子!」女人看玄武軍動作粗魯,急得要上前,被自己的男人攔住了。她和孩子不能有一丁點染病的可能。
裡間,那張被檢查過的床榻下,姜嬈爬了出來。
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攔,領頭的玄武軍越發覺得蹊蹺,也不等手下人進去,他罵了聲,一甩胳膊自己大步往裡頭了。
「官爺!」女人這時候抱著孩子衝上前去,她模樣有些慌亂,「官爺,行行好,我三嬸子經不起這折騰的,而且她得了病,那病會傳人的!」
被點中的兩個人又是緊張又是興奮,彷彿那榻上蓋在被子裡的不是一個人,而是白花花的一千兩銀子。
「這……」被點的玄武軍有些猶豫,被瞪了一眼,還是去了。
一行玄武軍將這戶人家的屋子攪了個天翻地覆,女人被氣得直哭,他們卻浩浩蕩蕩頭也不回地走了。
這張床的下方放了個大箱子,大約是收歸衣裳的木箱,她體型纖瘦,借著箱子堪堪掩住了身形,而床下太黑,木箱和床板幾乎混為一片,那玄武軍又看得匆忙,便無所察覺。
姜嬈拍了拍身上的灰,看向拉她進來的女人,語調有些猶豫:「多謝你們幫我,你們……是上殷人?」
按理說上殷人都藏起來了,如今這當口,更不敢堂而皇之地出現在玄武軍面前才對。
果然,女人搖了搖頭:「不……我們不是,我們是晉人。」
姜嬈愣了下:「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女人點了下頭,縱使面前的人髮絲拂亂,裙擺也髒了,可絲毫掩不住她絕色的姿容,女人似有些羨慕,又有些自卑,聲音低低道:「您是……是上殷的明華公主。」
如今孟家滿晉國地找她和齊曕,畫像貼得到處都是,不認得她才是奇怪。
可既然認得,為何還要冒險救她?
「你們……為什麼要救我?」
女人眼裡露出些感激,輕聲道:「之前官軍圍城,我們聽說他們是要屠城,為了殺上殷人也不管我們了……那時候,公主您站在城牆上,和清河侯帶著人保護我們呢……」
姜嬈沒說話。
她從來沒想過保護晉人,她所做的一切僅僅是為了上殷的子民。
這一刻,她忽然有些可憐這些晉人。國尚存,家尚在,可晉國的皇室並不在乎晉國子民的性命,為了爭奪帝位不惜對自己的百姓下瘟疫利用他們,軍隊更是野蠻粗暴,軍隊的存在並不是為了保護百姓。
名存實亡,和名亡實存,究竟哪個更可悲些呢?
「砰」一聲輕響,外間的大門忽地開了,屋子裡的人都嚇了一跳。
&1t;divnettadv"&1t;n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