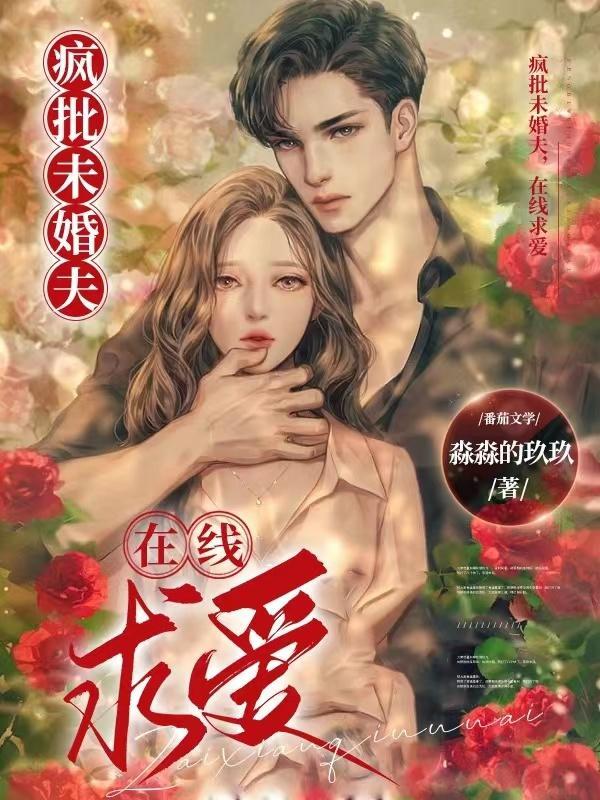笔趣小说>穿到权臣堆里玩厚黑学讲什么 > 第103章(第1页)
第103章(第1页)
邹清许忍不住清了清嗓子,他忽然想起刚刚和沈时钊交谈时,自己咳嗽了半天,可能那时暴露了他今天嗓子不佳的状态。
邹清许接过枇杷膏,说了声谢谢,但他目光看向的方向分明是沈时钊所在的方向。
沈时钊看上去不算坦荡磊落,神色也有些不自然,可能是因为刚刚捞了他一把,发丝有一点凌乱,但在他在气质和气势这方面一向拿捏的死死的,如月夜里的青松,站得笔直,黑眸晶亮如宝石。
贺朝的话时不时在他脑海里循环播放,他俩的传言是不是真的?
世人皆说两人是断袖,不然一个奸臣和一个清流,怎么可能天天厮混在一起?
长煜带着邹清许出门,邹清许摸着那瓶枇杷膏,魂不守舍。
快要出门时,他对长煜说:“告诉你家大人,再次感谢你们的枇杷膏,关于今晚我找他聊的事,我等他消息。”
长煜:“不客气,放心,慢走。”
邹清许往前走出几步后,停下来又回头说:“让你们大人不要担心,我嗓子没问题,晚上吃了辣椒,所以不太舒服。”
长煜点了点头,但他分外不解,于是脱口而出:“为什么要告诉大人这些?”
邹清许嬉皮笑脸地笑了笑,说:“总感觉他可能会关心我。”
说完,他拿着枇杷膏,转身,彻底离开沈府。
邹清许相信沈时钊,去沈府和沈时钊通过气后没再折腾,过了一阵儿,荣庆帝果真下令大查盐税。
此事一出,便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邹清许去泰王府的时候,泰王提到了此事,他问邹清许:“你知道这件事最开始是谁和父皇提的吗?”
邹清许的某些消息没有泰王丰富和及时,他大部分的情报全靠听八卦,邹清许表示自己不知晓此事后,泰王告诉他:“任循。”
邹清许大吃一惊。
他和泰王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各自无言。
邹清许的心虚在这一刻再次达到了顶峰。
沈时钊的处理方式出乎他的意料,没想到他默默无闻和任循牵上了线。
泰王:“你说沈时钊会不会知道了我们想干什么?”
邹清许低头思索,泰王脸色愁苦:“难道他知道了我们想拉拢任循,所以提前向我们示威吗?”
邹清许揉了揉太阳穴:“还有一种可能,他也想拉拢任循。”
这件事让邹清许感到惊诧,但又没有那么惊诧,沈时钊像狼,还像狐狸,当队友惹人爱,当对手惹人恨。
泰王:“既然如此,任循看来不值得信任。说实话,经过此事,他在陆党中的声望已经大跌。”
邹清许摇头:“陆党现在如同一盘散沙,总有一天会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我调查过任循这个人,他虽然不喜欢党争,但很懂时势,估计他觉得陆党没前途,想提前为自己找出路。”
邹清许更倾向于这是一次一拍即合的合作,沈时钊和任循各有所需,沈时钊需要一位有身份和地位、且刚直的人在荣庆帝面前提起此事,而任循需要在陆党倒台之后让自己能安身立命。
暂时看,朝堂将来一定是谢党的天下,何况谢止松还在陆党的刘琮阻止他入阁时把他引入内阁。
泰王担忧地问:“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邹清许眼前闪过沈时钊的脸:“先静观其变。”
内鬼
荣庆帝一声令下,都察院立马放手去干,荣庆帝专门传沈时钊进宫,让他一定要把大鱼揪出来。
小鱼小虾不成气候,抓大鱼才能解决问题。
董云贪污证据确凿,很快被缉拿归案。
成国公府接连安静了几天,看似平静之下暗潮翻涌。
董云心理素质强硬,他自己证据确凿,脱不了身,却一点没把成国公供出来,有证据的罪名他含糊其辞的认下,没有证据的罪名一概说与自己无关。
至于成国公彻头彻尾没有被卷进此事。董云不傻,留着成国公这棵大树,他以后还有翻身的机会,成国公倒下,他将彻底没有机会,何况自己全家的命都捏在成国公手里,他不能轻举妄动。
果然,因为董云的身份,没人敢过分为难他。
他可是成国公的女婿,得罪了成国公,日后能好混吗?
审理一度陷入僵局。
查封董云府里时,沈时钊约邹清许一同前往,邹清许不想抛头露面,在董府外面闲逛和打探消息,有时候证据不在府里,说不定在府外。董云家里奢华浮夸,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目光所及之处,处处是金银珠玉。
正当沈时钊在屋子里查得热火朝天时,邹清许在董府外面转悠,他仔细观察着董府外面的街道,和附近居住的百姓扯东扯西,试图套出一点东西来。此时,一个小妾趁乱躲到外面,被邹清许撞上,邹清许看这姑娘打扮的花枝招展,问了一嘴,得知是府里的人后,立马和人家聊了起来。
好巧不巧,邹清许盯上别人的时候,他也被人盯上了。
在府外蹲守的人看到邹清许鬼鬼祟祟,又看到他和小妾勾勾搭搭,二话不说走上前去一把拧过邹清许的胳膊,将他架了起来。
一股痛意从肩肘处直接传到天灵盖,邹清许两眼一黑,只听头顶传来一道声音:“你是谁?”
邹清许大喊:“误会!兄弟,一定有误会!”
对方看他不说,马上要加大力度,废他一条胳膊。
一旁的姑娘害怕的用手遮住嘴巴,不敢直视。
“说不说,不说你胳膊别要了!”
“说说说!”邹清许脑袋发沉,孰轻孰重他分得清,但绑他的哥们貌似不讲武德,仿佛不管他说不说,都要让他没半条小命,邹清许心想栽了,怕是要凉,然而,自己的胳膊轻飘飘落了下来,整个人被人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