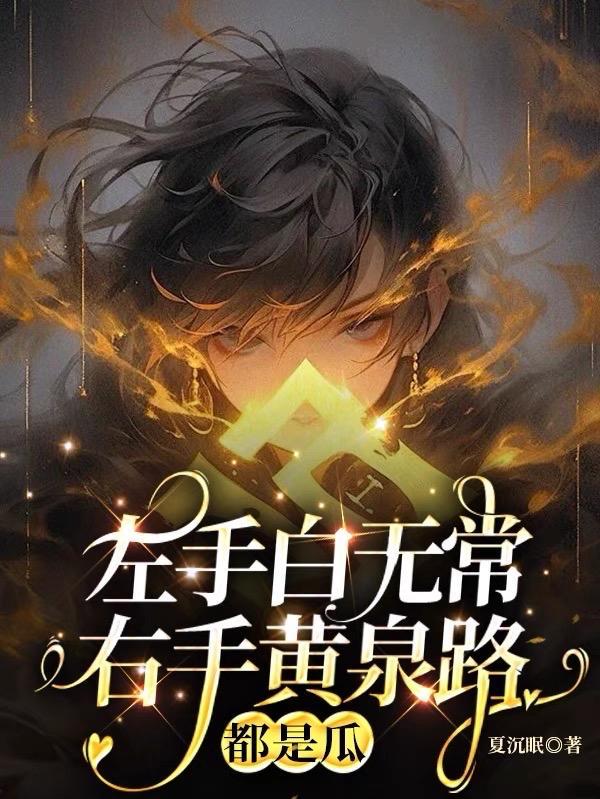笔趣小说>她为刍狗 TXT > 第21章 独身(第2页)
第21章 独身(第2页)
她走近容衣门前,轻轻叩门,“容衣,我来看看你。”
里面哼一声。
侍女得了应允打开门,刍狗走进去。
容衣如玉脂的鼻尖红,眼睛下挂着哭晕,气势汹汹又冷漠地哼了一声。
“你见我干什么?你来炫耀了?”
“我。。。。。。许多年没见你了,没和你说上话。”你就要被安排嫁人了。
容衣拧眉冷刺,“同我说上话你就得好处了?你敢叫我一声’妹妹’,占我和弟弟便宜!”
刍狗自卑垂头,“我、我不敢。”
“不敢什么?你厉害得很!”容衣讥讽,“我老早就认识仙臣哥哥,还不如你在药山暗暗的勾搭他,仙臣哥哥才练成剑术,心地善良经历也少,不知道你偷摸在外面怎么摇尾乞怜,不知矜持的迷住了他!”
其他女修们交换眼神,捂嘴笑起来。
刍狗转开脸看地,容衣顿觉恶心:“你的守宫砂呢?让我看看!”
刍狗退缩,“点砂要用水银。。。。。。。没给我点过这个。我跟伊公子没有关系。”
容衣想着自己竟成为崔氏的笑话,人生大事上被爹娘不管不顾的安排,悲从中来,溢出眼泪叫喊,“只有我喜欢仙臣哥哥,我却要和最讨厌的人成婚!”
刍狗的手臂忽然被容衣抓住,这是她第一次碰触刍狗,看她白软透香的手按住自己,刍狗惶恐无措。
容衣瞪住她,气糊涂了似的叫:“你给我气死崔心夷,你就赖在仙臣哥哥身边不走!”
刍狗灰了心,乞求道:“容衣,我只是个短寿的凡人。”
你让我送死。
容衣的新泪干在眼皮上,厌憎地推搡瘦弱的她,“你为何一点灵力也没有?你但凡有一点点灵根,现在怎么是这样?拖我们的后腿,丢父君母亲的脸,给五姓添笑料!”
“我不拖累你们了。”她垂下眼皮,静静的说,“容衣,我现在回药山种地去了。母亲大约也不喜欢我在寿宴上出错,你跟母亲说说好吗?”
容衣翻个白眼,不知道听没听进去,迁怒的为自己姻缘痛苦脾气。
刍狗看着众人小心翼翼忙碌着伺候抚慰她,默不作声的主动消失。
回到自己清冷寂静的闺房,她脱掉外衣,把没有热气的脚放进被子里暖住。
还是从来没人在乎她的安危死活。
刍狗从身体凉到了心。
如果没有救过伊仙臣,她假装继续和行尸走肉们死在药山,后续不必受这么多侮辱嘲讽。
她睡了一两个时辰,换回自己做的布衣布裙,归还上官家族的服饰,现少了一条竹叶纹绣的手帕。
那条手帕是脚扭伤疼痛的时候,她用来包裹肿了的脚踝的,免得和鞋摩擦刺激得更疼。
她怎么也找不到那条手帕在哪里。
刍狗慌张,不会是被伊仙臣握住脚治疗时,落到他身上了吧?
她尴尬又沮丧,这段伤人的孽缘彻底终止,不要再见了,让它死在旧时光里,不再牵缠作乱吧。
她等了一天,父君和母后没有传来口信,回应她的告辞。
没有回应,也没有人问她。
她去请安问候,也不让她进去。
刍狗委屈泣涕,清点身上的银钱。
她离开上官的宫府时,没有人拦她。
朱门闭合,刍狗在麒麟石像后,茫然孤独地看着官贵连通家臣世家府、如银如雪的金丝白玉石长街。
京都往药山三千里路,她靠一双凡人的腿,在外面雇上马车,两年也走不到。
况且她一个独身的凡人女子行路,会受到很多骚扰和麻烦,也会落入危险。
她往京都外走,脚步停在母亲的娘家卢氏府前,忽然看到卢义誉醉醺醺地出来送人,明显是卢家过年时在家中置宴待客,陪酒之后送客人走。
刍狗咬住嘴唇,远远望向卢义誉。
至少这位表哥还会笑着跟她客套说话。
也会调戏勾引她,言语中占她便宜。
她摸起身上有没有对修士有用的灵物灵植,总得有一物请得动修士用法术帮她回去。
她把装进药山收获的储物戒给少君弟弟喂马烧炉,便什么都没有了。
刍狗不知怎么办才好,卢义誉已经歪着脚步准备进卢府的门。
“卢表哥。”
她紧急叫出声。
卢义誉回头,看到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