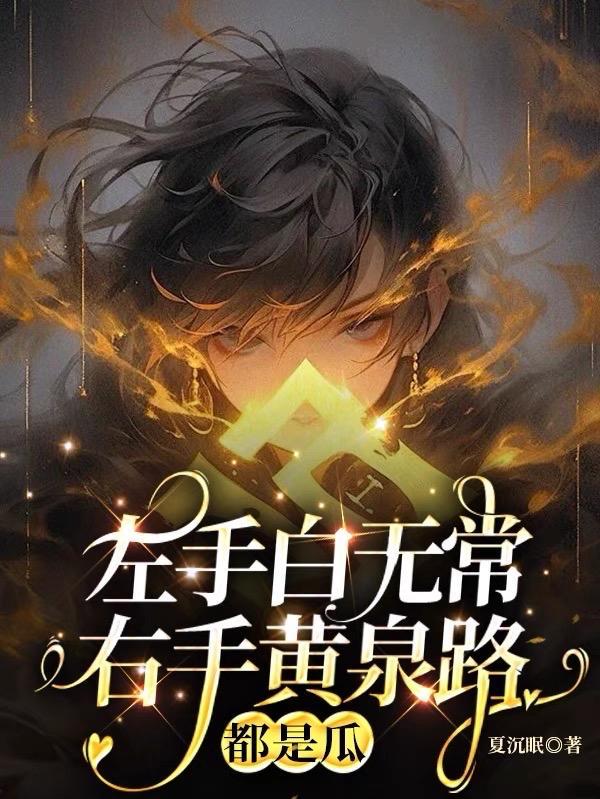笔趣小说>暗恋暂停开始恋爱短剧 > 第327章(第1页)
第327章(第1页)
是沈聿刚送来的那两瓶。
他气笑,防得了念念不忘的岳子封,没防住他心血来潮的太太。
“知道这是什么酒吗,你就喝。”
霜序把一杯递给他:“酒不就是用来喝的?”
说得有道理。贺庭洲把杯子接过来。
霜序记得沈聿说过,她出生那年因为洪水导致酒庄被淹,存留下来的酒很少,味道也受到影响。
她先闻了闻,香气还不错,杯子送到嘴边,她慢慢品啜一口,眉心轻蹙起来。
“这个酒果然不好喝。”
贺庭洲倚着桌子,尝了尝,这瓶酒口感的确一般,单宁的苦跟涩感都偏重,熬过起初的那阵酸苦,便是余韵悠长的甘甜香气。
入口不够顺滑,但有着复杂的层次,苦涩之后反而会给人更多的惊喜。
贺庭洲说:“我很喜欢。”
“真的?”霜序看他喝得津津有味,觉得是不是自己的结论下得太草率,又试了试味道,再度拧眉,看他的眼神充满怀疑,“你是不是味觉失灵了,一点都不好喝。”
贺庭洲:“我说我喜欢,没说它好喝。”
“不好喝你还喜欢?”
贺庭洲把她勾到身前抱着:“谁让我爱上一个苦瓜。可能我天生爱吃苦吧。”
明明是一个爱吃糖和甜食的人。
霜序把蛋糕端过来,两个人用叉子分食着同一只蛋糕。
宾客们还在宴会厅为这对新婚夫妻庆贺,而他们两个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蛋糕配红酒。
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那瓶红酒再喝时,霜序品尝出了些不一样的风味。
一瓶酒见底,她忽然间来了创作灵感:“下次给你做个苦瓜蛋糕吧。”
贺庭洲被她歹毒的创意弄笑了:“你是对我有意见,还是对蛋糕有意见?”
霜序歪头:“你不是爱吃苦?”
贺庭洲把她手里的杯子和蛋糕碟拿走放到一边,抄起她腿弯把她抱起来。
霜序也不挣扎,熟练地圈住他铂晶。
贺庭洲抱着她走进卧室,丢到床上,她在床垫上弹了一下,人还没来得及坐起来,就被他按了回去。
他的手在她腰上的痒痒肉捏了捏,霜序就开始像条鱼一样在他怀里扑腾起来,笑得脸都红了:“痒,别弄……你干嘛啊!”
“找找开关。”贺庭洲说,“我的甜瓜公主呢?”
“……”
*
婚礼是一个可以尽情放纵的日子,在这一天喝醉,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哪怕是沈聿这样极少失态的人。
他喝得酩酊大醉,是岳子封送他回的家。
翌日醒来已接近中午,宿醉后的头痛伴随着一种从骨头里透出的疲乏。
他走出卧室,去倒了杯水,窗帘紧闭的客厅里光影昏沉,沈聿打开窗帘,沙上岳子封呻吟着坐起来:“卧槽,我的腰……”
“你怎么在这?”沈聿问。
“你还有脸问,你昨天醉那么死,我怕你半夜吐死了没人给你收尸。”岳子封揉着腰从沙上起来,“有吃的没,给我弄点吃的。”
“龟粮你吃吗?”
沈聿站在生态鱼缸前,拿着一只精致的镊子,正夹着龟粮给乌龟喂食。
岳子封一脸纳闷地凑过去:“你什么时候养的乌龟?”
“三个月前。”
这只龟圆头圆脑,长得挺可爱,岳子封认起来了:“这是妹妹以前养的那只吧?不是丢了吗?”
沈聿没否认,喂完乌龟,把它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晒太阳。
这只乌龟在霜序从沈家搬走的那一天莫名失踪,半年后又神奇地出现,兴许是因为燕城的冬天太冷,西非侧颈龟并不耐寒。
没人知道它去了哪里,这半年经历了什么,它毫无征兆地消失又自己平安归来。就像它的名字,叫归归。
现它的时候,它在霜序房间的洗手间里,王嫂慌忙把它抓起来,跑来问沈聿:“要不要给霜序小姐送过去?”
沈聿说不必了,她不需要了。
她的鱼缸已经搬到太和院,里面养着贺庭洲送她的那条鱼。
沈聿把乌龟带回自己的公寓,买了生态鱼缸养起来。
它无忧无虑,每天除了吃龟粮就是晒太阳。
这种乌龟的寿命有3o到5o年,它还有很长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