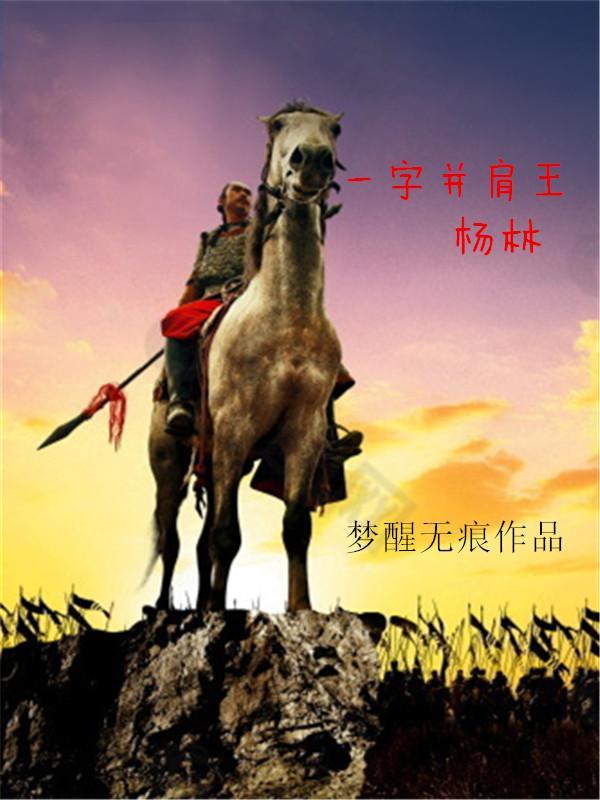笔趣小说>嚼龙爪菊能治疗咽炎吗怎么吃 > 第37章 以观后效(第2页)
第37章 以观后效(第2页)
在山里时,焦玉浪已经给他灌输了一大通江湖术士命贱如野狗草芥的论调,有镇魔院在,江湖术士乃至寻常的修行人轻不敢招惹朝廷官员,路云子那厮猖狂一时,还不是中了埋伏,险些身死道消?
哪怕他齐敬之是个不知晓镇魔院厉害的愣头青,侯长岐也大可以请孟夫子代为转圜,总能保住几分体面不是?
眼见侯典史这般低声下气,齐老汉一生豁达,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性子,肚里的气已经消了大半,只是他人老成精,知道典史老爷冲的可不是自己,也就没有急着开口,而是扭头看向了自家孙儿。
齐敬之则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了身旁未曾开过口的孟夫子,毕竟这位老师似乎与侯长岐有些交情,总不好让他面上太难看。
孟夫子感受到学生的目光,当即微微一笑,淡然说道:“看我做什么?这是你自家的事,自己做主便可。”
齐敬之点点头,看着依旧长揖不起的侯长岐道:“些许恩怨,我阿爷从没放在心上。可既然侯大人说恨不得以身相代,便也受二十脊杖好了,免得悔恨难消、日日牵肠挂肚,那反倒是我们爷孙的罪过了!”
他这话一出,熊太丰和万都头的脸色不免都有些难看,孟夫子和焦玉浪却都是一副早知如此的模样,齐老汉则面露忧色,欲言又止。
侯长岐猛直起身来,语气略显僵硬朝熊太丰道:“还请县尊允准,侯某这就去唤两个衙役到后堂来。”
他的肤色本就有些黑,此时脸色明显又差了几分。
见侯典史当真要自领脊杖,在座之人都有些吃惊,目光齐齐汇聚向齐敬之。
齐敬之神情自若,轻笑道:“我的话还没说完,前些日子侯大人已经答应免去我家的差役,阿爷和我自当承情,这脊杖……”
少年话未说完,熊太丰已是抚掌大笑:“这脊杖不如就免了!贤侄以德报怨,当真是豁达!老侯快快入席,咱们一起再敬贤侄一杯!”
万都头也连忙上前,伸手就要将侯长岐往座位上引。
侯长岐却是一摆手,摇头道:“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这二十脊杖,本就是侯某应得。”
这人也是有,让他领脊杖,眉头都不皱一下就一口答应,不让他领反倒不乐意起来。
齐敬之眸光一闪,当即点了点头,欣然道:“侯大人如此肯担当,我们爷孙理应成全,那就请吧。”
这话一出,满座皆寂。
饶是熊太丰这个人情练达的老油条,此刻也是一脸错愕,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侯长岐更是僵在原,难掩脸上的尴尬之色。
“啪!”
孟夫子忽然将手里的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搁,出了一声脆响。
待众人看过来,他才开口笑道:“侯大人,我这学生恩怨分明,又最是孝顺,今给你这个难看,也是你理亏在先,可不要往心里去。方才县尊已然下话来,还是快些落座吧。”
说罢,他朝万都头使了个眼色。
万都头登时会意,见齐敬之没有要反对的意思,不由分说便将有些失魂落魄的侯典史按回了座位。
齐敬之冷眼看着他,主动开口道:“侯大人,今日是熊县尊好意设宴、我师孟夫子作陪,我阿爷又最是心善不过,我看在他们面上,才想饶你一遭,谁知你得了便宜偏要卖乖!既然如此,那二十脊杖权且记下,日后若还敢欺压到良善百姓头上,再与你一并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