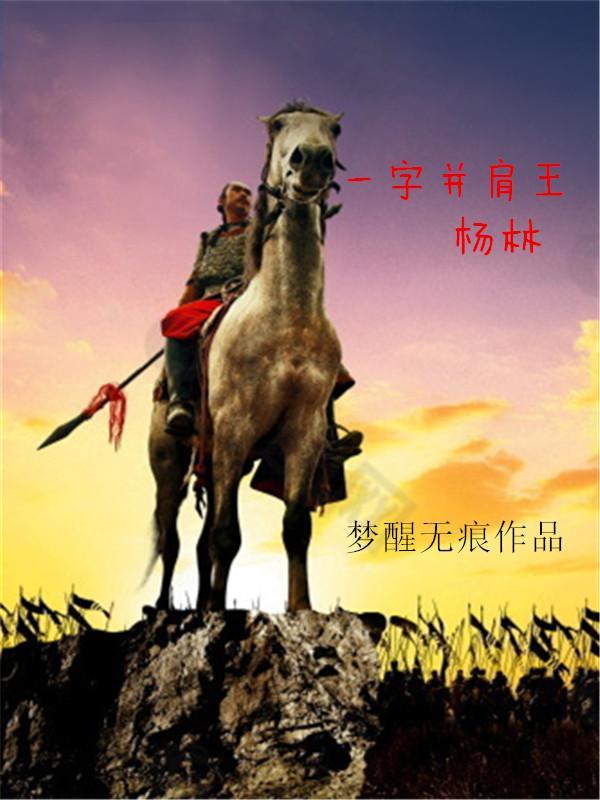笔趣小说>钟意生日 > 第71章 志向(第2页)
第71章 志向(第2页)
钟意笑道“告辞。”
二人一道出了前厅,钟意向前,陶肃右行,似乎是想起什么了,他忽然停住脚步,回身唤道“居士且慢”
钟意停住,问道“怎么,陶刺史有何见教”
“见教不敢当,”陶肃面上有些为难,顿了顿,还是道“居士肯献出钱粮,这是大恩,然而石州受灾严重,这些怕也只是杯水车薪,即便将州郡粮库中的存粮全部送去,怕也还查着些,更别说石州地处北境,需得筹措军粮,不敢全都用来赈灾”
钟意隐约猜到几分“陶刺史的意思是”
陶肃踌躇道“本地豪强大户颇多,家中也有余粮万千,我想请居士前往劝说一二,便以州郡名义相借,待他州钱粮到了,再行偿还,连本带息,绝不亏欠。”
“不是我不想帮,而是有心无力,”钟意摇头失笑“陶刺史在此任职几年,尚且说不通,我怎么能说通”
陶肃面上有些犹豫,迟疑片刻,方才道“那是清河崔氏的分支,居士母家乃是博陵崔氏,好歹皆是五姓亲族,我出自寒门,委实有些”
士庶之别,如同天堑,并不仅仅是官位高低所能改变的。
钟意也明白他的难处,然而没有把握的事情,却不敢满口应下。
“我只勉力一试,却不敢应承,”钟意只能道“尽力而为而已。”
“不敢,”陶肃长揖至地,再三谢道“居士肯去,我已经感激不尽。”
博陵崔氏与清河崔氏的先祖原为兄弟,汉时兄长崔业袭爵,居于清河,他的后代便是清河崔氏,其弟崔仲牟则另居博陵,其后代便是博陵崔氏,一笔写不出两个崔字,然而传续几百年,这两支的关系却很微妙。
李唐天下初定,皇帝令编纂姓氏品阶,因博陵崔氏与关陇贵族亲近,便以其为天下第一姓氏,皇帝闻之大怒,令皇族李姓为第一等,皇后何氏次之,第三方为崔姓,可即便如此,仍不能改变天下士族固有的观念。
而这个崔氏,实际上是指博陵崔氏。
同姓不婚,即便彼此的血脉已经淡化到相当境地,两家也无法婚嫁联姻,更没有办法彼此融合。
再加上评定姓氏品阶这缘故,博陵崔氏与清河崔氏虽同为五姓之一,关系却有些尴尬。
这也是同为一姓,钟意却过门不拜,甚至不知此处有清河分支的缘故。
陈实练达,便被钟意留下,负责监管钱粮诸事,其余侍从同她一道,另有刺史府中人引路,带着她往此地崔家去。
“居士,”玉秋犹疑道“要不要先送拜贴过去如此前往,恐有失礼之嫌。”
“事急从权,哪里能顾及这么多”钟意道“陶刺史是借,并非索要,且是用以赈灾,他们若是通情达理,必然肯借,怎么会介意一点小小失礼若是不肯,那即便投了拜贴,怕也无用。”
“居士何必这样操劳,”玉夏则道“将自己私房捐出去也就罢了,还这样奔走。”
“能多做一点也好,反正于我而言,也并不难,积德行善,总不是坏事,”钟意道“兴许我早些促成此事,便会少饿死一个人。”
玉秋笑道“居士是真正的慈悲人。”
钟意摇头道“那倒也担不起。”
“我也曾自怨自艾,天下这样大,为何只我会受那么多苦,可是后来见得多了,才知道我所经受的那些,根本不算什么。”
那些掩藏在记忆中的过往,都曾是她不愿提及的伤痛,然而到了此刻,全然释怀时,却觉满心轻松。
催马向前,她道“士兵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有时甚至连尸身都无法带回,只能就地掩埋,魂归千里,灾民在饥寒中慢慢死去,饱受折磨,那苦痛也并不比我少,这世间其实有许多远比我不幸的人。”
“我忽然间,想为他们做点什么,”钟意平和笑道“曾经有人告诉我,污迹是无法彻底擦除的,但并不是无法遮蔽。”
玉夏好奇道“那要怎么做呢”
“用令人不可逼视的光辉去掩盖它,用世人皆知的功绩去淡化它,我从前只是听,却不明白,直到突厥军营中脱身时,才醍醐灌顶,忽然醒悟。”
为什么前世没人在意她,东宫臣属们,即便满脸敬重,口中尊称,也不将她放在眼里
无非因为她的光芒皆是来自李政,她是打着李政标签的女人。
假如她能建立起不逊于李政的声名与功绩呢
那便是李政配不上她了。
“我不是男子,无法征战沙场,建功立业,但也并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钟意笑了,那笑容中有些希冀,还有些期许“立德、立功、立言,这是圣人所说的三不朽,谁说只有沙场征战才行”
从没有女人做过这样的事,那我便来做第一个。
我要这片土地上镌刻我的功绩,要这青史,记住我的名姓请牢记收藏,&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