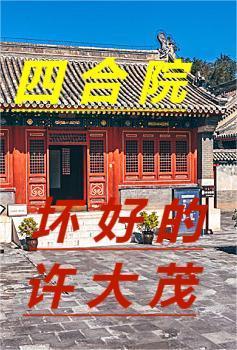笔趣小说>偏偏沦陷免费阅读 > 第102章(第2页)
第102章(第2页)
屋子外也围着人,这么多保镖守着一个生病的女人,有些大费周章。
而且被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吃饭,心里不自在。
沈辞留意到小姑娘的分神,夹了块鱼肉放她碗里,询问道:“怎么了?”
路桑下意识瞥了眼保镖,摇头说没什么。
她乖乖吃着饭,竭力忽略那种不适。
沈辞眼眸暗了下,舌尖舔了舔后槽牙,嗓音有点冷,但还算客气:“麻烦你们出去一下。”
上扬的音调能让整个客厅的人都能听见。
保镖们岿然不动,直到沈辞眼神一冷,筷子撂下。
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少年就不是好惹的主。
有个男人上前,一字一句道:“沈少,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去,实在是沈总的命令不好违抗,大家都是要吃饭的人,上有老下有小,还望您理解。”
沈辞攥着水杯的手指握紧,骨节泛白。
凛冽的下颌线也绷紧,眼皮里是压不住的戾气,好像下一秒就能爆发。
倏地,冰凉的手背覆下一层软乎的温暖。
路桑轻轻握着他的手,抬眸看他,用温和的声音说:“阿辞,你,你别生气。”
她温软的眼神像是有股魔力,沈辞吸了口气,那股汹涌的烦躁逐渐散去。
连周身的戾气也收敛了不少。
“好。”他哑着声回应。
吃完午饭,周妈把他们送到门口,一番贴心的叮嘱后,恋恋不舍地告别。
上车后,沈辞从裤兜里摸出一根烟,许是顾忌到小姑娘的存在,他没抽,指尖摩挲着烟身,嗅了下。
眼眸幽深,嗓音低沉,缓缓解释道:“那些人是我爸派来的,目的就是用我妈牵制我。”
打蛇打七寸,沈母是沈辞的软肋,沈辞又是沈老爷子的软肋。
沈临舟打了个好算盘。
路桑扒着车窗看,透过玻璃,看到院子里栽种的腊梅开了,霜雪的衬托下娇艳美丽。
纪时纾年轻时是个富有生活情趣的小女人,花园里还种着各种花卉绿植,来年春天万物复苏,应当极美。
刺骨北风夹着雪粒刮过,眼前的春花烂漫烟雾般散尽,霜雪笼罩,枯木狰狞,萧瑟伶仃。
像一个冷冰冰的牢笼。
牢笼里伸出一根漆黑的铁链,拉扯着雏鹰的翅膀。
它飞不高,也飞不快,一动就遍体鳞伤。
……
车子离开了小洋房,往沈宅驶去。
地方是寸土寸金的别墅区,门卫身上穿着军装,挺拔而立,一派庄重严肃。
古朴的铁门缓缓往两边打开,一路上有植物修剪的雕塑和水花四溅的喷泉,车子在繁密的林叶间又行驶了会儿,才到达地方。
还没下车,沈辞的手机就已经被一百零八次轰炸。
“你小子,不是说好带女同学来家吗,人呢?!”
沈辞捂了下耳朵,中气十足,看来老头身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