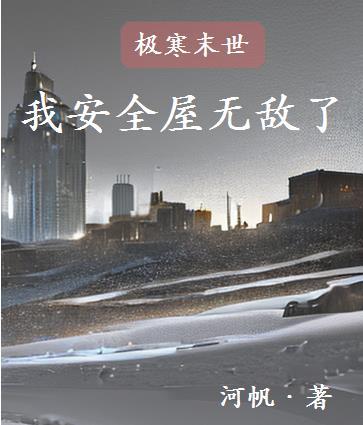笔趣小说>明月台赋全文免费阅读TXT > 第77章(第1页)
第77章(第1页)
殿外自然是送他回边疆的人,一番折腾后一无所得地被送回那边陲之地,于他那种野心勃勃之人来说,倒更像是讥讽。
“就将他这么原封不动的送回去?”伽殷走上前来,与我并肩而行,“嫂嫂,我怕有些不妥。”
“什么妥不妥的。”我笑道,“他为了王位疯迷,我非要让他明白,自己哪怕穷尽一生也永远得不到所求之物,这才是最让他痛苦的事。”
不断挣扎、算计,然后一次又一次在即将功成之际功亏一篑,进而为此耗尽一生却始终一无所得,岂不比一刀了结他更让人痛苦?若是下次还来,继续放他进来就是,届时再叫人捉住送回去,我不信他心中不煎熬。
再说了,此时就算想杀他,我的手也不便沾染鲜血。
我们正走着,忽闻身后传来一声冷淡的“沈鹤眠”。回眸看去,是伽宁。
她那张尚未长开的面上透着无边的清冷,薄唇轻轻向下垂着,颈上裹着一道白绸。
伽殷正要张口斥责她无礼,我按住了她的手,示意伽宁继续说。
“替我寻一座佛堂。”
我心底有些诧异,道:“伽宁,我不会苛责你父亲,亦不会追究你的所作所为。将来议亲也好,婚嫁也罢,我和你王叔必然会亲自为你做主,你大可安心在宫中住着。”
“不必,”伽宁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声音沉静如水,“我看着你们斗来斗去实在是累得慌,不如尽早抽身。从此斩断红尘、潜心静修,将来你们谁输谁赢,都与我无关。”
“你父亲他那是用刀,并非是……”我还想说些什么,伽宁却径自从腰间摸出一把精巧的袖珍小刀,削去了自己的一缕。
伽殷与我对视一眼,无奈地摇了摇头。
“她先前在我身边教养,就已经有些心灰意冷。”她拉着我往回走,“走到这一步,实在是无人能解她心结了。”
“在宫中修一座佛堂,派两个与她亲近的女奴跟着罢。不必住到宫外去叫众人都知道,若是将来长大了想要还俗,也容易些。“”一时间,我心中感慨万千。
从前孤身在渊宫里看着宫中人明争暗斗,我亦有时百念俱灰,后来跟在伽萨身边才逐渐变得鲜活起来。
如今只能盼着,将来伽宁也能碰到融化她冰心之人,
“之后的事就麻烦公主了。”我步至阶下,“我还得回去。”
“嫂嫂手上有急事?”伽殷问。
“也不是什么大事。”我笑笑,告了辞。
-
说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也不过是沐浴,焚香,拜佛,积德,祈求伽萨在边关一切安好。
我遣散众人,手中捏着三炷香独自跪在蒲团上,拜完元始天尊拜如来佛祖,末了又拜观音菩萨,最后连着那妖里妖气的金身蛇像也供奉了香火。
“公子从前不是不信这些的么?”容安见我出来,悄悄地问。
“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我拂去袖上的香灰,道,“我如今就爱信这些。举头三尺有神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正巧,桑鸠捧着个红木漆盒迎上前来:“公子前些日子托人雕的黑耳大猫像,方才有人送来了。”
我两手一拍,将那盒子打开一瞧,果然是栩栩如生的一只黑耳猫,身着玳瑁斑纹,两耳垂下黑色长毛,怒目圆睁,威风凛凛。
“公子,这是什么猫?看着又像豹子又像狐狸的。”容安好奇地把那大猫大量了好几眼,半躲在我身后又怕又想瞧。
“这是番邦的黑耳猫,传说能扑杀食蛇鹫,拗断它们的翅,撕碎它们的爪。”我示意桑鸠将雕像摆进房中,“很是凶猛威武。”
桑鸠行了个礼便进了屋,容安回眸盯着那像望了许久,又道:“公子是记着文吉人信奉食蛇鹫,所以才特意寻来这大猫像的么?”
我心中有些不好意思,略略忸怩了片刻,道:“刀剑无眼,我只盼着他在沙场之上好好的,千万不要受重伤。”
月亮渐渐上了半空,我坐在屋檐下,定定地望着那轮圆月。
人人都说明月寄相思,可我偏不敢思念他,怕月光扰了他的心绪。
容安席地而坐,陪我一同望着天上的月亮,低声道:“公子是想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