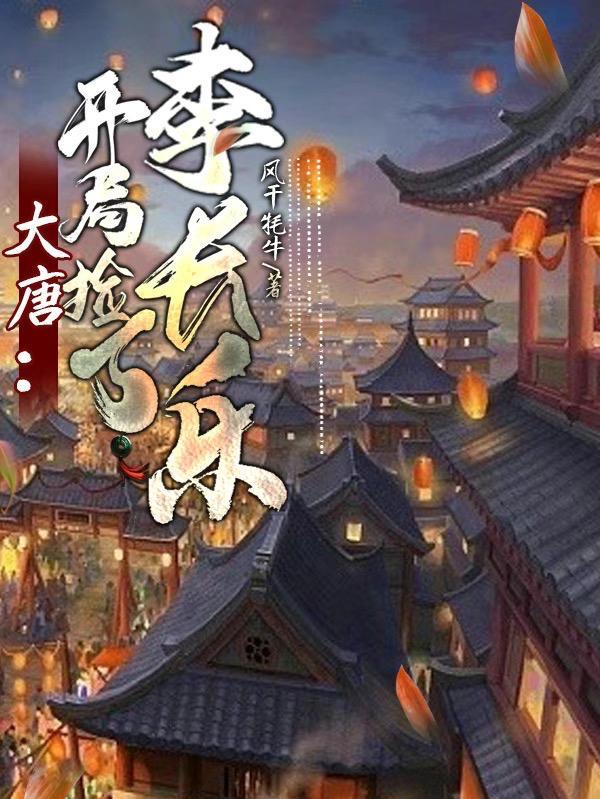笔趣小说>鸦渡什么意思 > 第17章 多谢公主赐教(第1页)
第17章 多谢公主赐教(第1页)
季如光没想到她回转地如此痛快,抬手悬在半空,一时有点迟疑。
符寿安反而竟直接拍了上去,纤纤素手透着凉意,却毫不示弱,用足了十分力气。
“成交!”
“殿下就不继续追问,我图的究竟是什么?”
“哼!有什么好问的?”符寿安拿起案报,头也不抬:“横竖你助我离开在先,之后你图什么,又是另一桩生意了!”
季如光顿时无奈,这个公主,果然不好招架。
玉纯悄悄凑近符寿安,有些忐忑。
“殿下,眼下情势复杂,仅凭他一张口,便答应了么?焉知他不是以口舌作诱,拿话套我们,临了又返给太子?”
“放心吧,我心里有计较。”
符寿安拍拍玉纯,出言安慰。
答应季如光,自不是符寿安热血上头,也不是她心存侥幸。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季如光此人,心思深沉,目光犀利。
她的全盘逃跑计划刚好都落入他的掌握。
私改观内布局,囤积引火之物、玉清在贵妃面前的假死、对办案主官设局动刀子……哪一条报上去都能让她万劫不复。
她似乎被彻底拿捏了。
但现实又能证明,季如光并不是敌人——他对太子麾下丝毫不假辞色。抛下雷敬让她瞧,带来全盘案报,所有地方都体现了诚意。
最重要的是,若不是有及重要的事,谁会愿意与一个不相干的人同缚共死?
通关了全局,她的棋盘上,只找到了这一座生门。
一炷香毕,她已经读完了所有的案报。
“如何?”
季如光颇有些期待。
符寿安指着案报上福生的名字:“这个人,可以提来让我看看吗?”
季如光看了公主一眼,有点意外。
案报里只提了生的事情,却并未包含分析判断。
符寿安能从这些文字里现蛛丝马迹,其心思缜密灵动,着实高于常人。
“这个福生,是贵妃娘娘最为得力的女官,这些年来为主人赴汤蹈火不说,还搭上了东宫太子。只要仰仗这对母子,便会有大好前程,于情于理,她都是最不可能杀害贵妃的人,甚至两桩案子生时,她都不在现场,公主为何怀疑她?”季如光试探道。
“因为身份。”
“身份?”
“嗯。”
符寿安点点头,“原来她是前礼部尚书赵奇瑜的嫡亲孙女。而赵奇瑜和他儿子被罢官斩,赵家被抄,都是我看过之后几日内生的。”
“公主怀疑作案之人,是为了复仇,所以构陷于你?”
季如光虽觉得有点意外,但细细一想,也不是没有可能。
符寿安继续说道:“我自小便有这奇异本事,也不知是娘胎里带的,还是吃了什么桃儿果儿生出来的。”她将案报摊在手中,一遍遍地翻,目光却在别处。
“在这观里长到十岁,父皇便总是和范公公一起来,命我看一些人的眼睛。我记得,都是些老头子,有的是文官,有的是武将,甚至还有一位皇叔,颍川王。他们进来时,有的只说来祈福,有的,却已剥去了官服官帽,浑身血淋淋的。”
季如光静静听着她讲。
语气冷静,没有起伏,所说之事,却全然与骄矜少女的生活毫不沾边。
对这些事习以为常,何尝不是一种残忍。
“父皇之所以要我看,有的是谋反却找不到书信往来,有的是贪弊却寻不见金银所在。最奇的是,有的只是见了什么人,哪怕那人不承认,父皇也会勃然大怒。”
符寿安抬头看着季如光。
“他们之后的结局,父皇从不跟我提起,我都是让玉真她们悄悄四下打听,才偶尔得知,他们或被罢官流放,或被满门抄斩。倒是从没想过,这些人竟还会有家人,留在宫里。”
季如光点点头:“公主进寿安观的时候还小,不知也属正常,本朝惯例,勋贵重臣若是犯了大罪,男丁抄斩,成年女眷充军,直系子孙若在十二岁以下,无论男女,皆抄没入宫。”
“这么看来,福生昨日来见我时,气势汹汹的模样,倒也不全是倚贵妃的地位耍威风,而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罢了。”符寿安苦笑:“此人你们可审过?”
这下轮到季如光苦笑了:“我们虽未想过罪臣之后复仇一事,却也觉得福生甚为可疑。可太子将她护得很紧,没有确凿破绽,我们净尘司也动她不得。”
“没想到净尘司看起来威风八面,办起案来,也是如履薄冰,各处掣肘。”符寿安感叹一句,同情大过了揶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