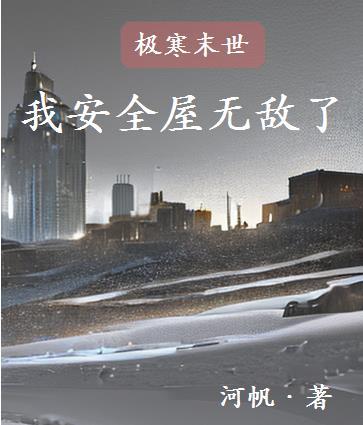笔趣小说>权臣妻控男主身世 > 19心病(第2页)
19心病(第2页)
今年,成州一带出现神秘墨客辗转经营,联络朝廷官员,试图寻找当年新政党的幸存者,而此次成州流民作乱反叛朝廷,也很难说是不是受这群人的蛊惑。
梁潇坐在书案后良久无言,手摩挲着邸报上“幸存者”三字,忽得抬头问“虞清还打探出来什么”
书房里跪着军中信使,受左翎卫将军虞清所托,不走官道,秘密进京向梁潇禀报军情。
信使道“虞将军怀疑,京中亦有新政党在暗中行事,策应成州。只是将军远在千里之外平叛,无暇顾及,特命属下进京提醒殿下,此事敏感,涉及靖穆王府,您千万要小心。”
梁潇点了点头,让信使稍作休息就回成州。
他将邸报扔回书案,起身走到窗前。
天边彤云密布,阴影自重檐覆屋游移,逐渐扩大,枝桠迎风簌簌颤立,瞧上去是一场大雨。
方才还是春风艳阳天,顷刻间就变了脸。
站了好一会儿,听见身后有衣料窸窣的低微声响,他头都没回,直接问“阿翁,怎么了”
姬无剑道“玉徽县君闹着要见您,王府护卫已奉命将她拦下,您看”
梁潇揶揄“她是要见我吗是挂念着她的墨辞哥哥吧。我可没有姜墨辞的福分,有那么贴心为兄的好妹妹。”
姬无剑不知该说什么,听得梁潇凛声吩咐“把她轰出去,这些日子不许她来王府,还有”
他顿声,添了万分的凝重“加派守卫,守好暗室和西厢,一定要看住了姜墨辞和谢夫子。”
本以为关他们些日子,待成州战事彻底结束便放他们回去,如今看来是不行了。
成州是一滩浑水,金陵也不见得干净。七年前姜墨辞在京中为质,辰羡和新政党的活动他参与的并不多,怎得就能轻易找到那间专供秘密联络的小院子
最坏的答案,就是七年后的今天,姜墨辞又重新和那些人搭上线了。
可姜墨辞既然参与新政不多,认识的新政党也不多,那有谁会是他恰恰认识,又能如此信赖的呢
梁潇胸膛堵着一口气,狠狠打在金交椅背上,怒道“给姜墨辞上点刑,审他,如果还审不出来,就把谢夫子拖过去,看这一对苦命师徒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姬无剑瞠目“这,王妃那边”
“别让她知道,还有,刑具上收着点劲,别给姜墨辞留下残疾。”
这么打定主意,梁潇难得慈悲大,真让姜墨辞和姜姮见了一面,姜姮见姜墨辞虽胡子拉碴狼狈不堪,但衣上一点血渍都没有,终于能放下心,也不再闹,肯乖乖地喝药。
只是她不知道,姜墨辞一离了她就被带去暗室受刑。
这些日子朝廷风云不歇,王瑾见抢夺军权不成,上奏说近来京中仕子妄议朝政的现象时有生,让京兆府和大理寺严加查探。
这等鸡毛蒜皮的事梁潇不欲理会,由着他去,只是今年本是大考之年,仕子齐聚京都,须得暗中看着,别闹出乱子才好。
天气渐热,侍女拿几把孔雀翠尾帚在阶前除尘,寝阁内馨香靡靡,瓶花鲜活沾露,桃红罗帐荡如秋波。
姜姮隐约觉得梁潇有心事,床上摧折起人来愈凶狠,待风停雨收,姜姮只觉油锅里滚了一遭,伏在枕间虚弱的喘息。
但今日梁潇却仿佛极有兴致,没有立即叫水,反倒凑上来吻她的脸。
缠绵细碎的吻,带着些疲惫,些留恋。
姜姮温顺地趴着,任由他施为,许久,听他在耳畔问“姮姮,你会离开我吗”
呵姜姮心底嘲弄,答得却顺畅“不会。”
“是啊,你不会。”梁潇仰躺在她身侧,勾缠起她的一缕秀把玩,漫然道“跟我睡了七年,还有哪个男人会要你,敢要你。”
姜姮觉得他很可笑,却又懒得剖析他可笑在哪里,翻过身将自己裹进被衾中,闭上眼想睡。
夏日渐迟,天甚至还是亮的,就被梁潇拖着逼着来了这么一场,骨头都似快要被他碾碎了。
梁潇以手擎脑侧,半抬起身看她,状若随意道“那若是辰羡呢”
姜姮猛地睁开眼,转动眼珠看他。
“若是辰羡没死呢”
梁潇紧盯着姜姮的脸,观察她的神色,半晌才道“当年他被关在大理寺天牢里,我察觉到外头有人想营救他。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为什么不去救卫王,但那段时间天牢里确实出了些事,不怎么平静我拿不准,但我总觉得,这些年辰羡没有走,一直躲在一个地方看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