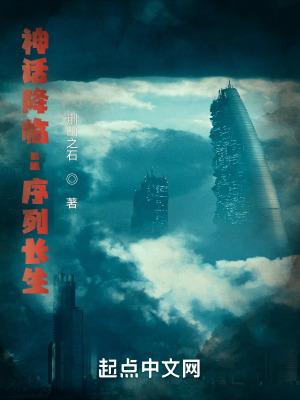笔趣小说>我成了他的后妈 > 第92章 就此别过(第2页)
第92章 就此别过(第2页)
可我怎么解释?拔出萝卜带出泥,解释了这个,就得解释我妈在锤什么。
解释了那个,我跟梁墨冬会掰得更难看。
我一路来到单元门门口,但没有进去,就在电动车后头的石头上坐下了。
透过电动车的缝隙,能够看到,那科尼塞克始终停在原地,漆黑的车身,如一只蛰伏在积雪上的巨兽。
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进去。
他现在很不冷静,我不想让他开车。
而现在天黑了,只要我不进屋,不开灯,他就不会走。
一如小时候,每次等我进了巷子,到家之后,都能看到他在巷子口等着——等到看到我家开灯,他才会离开。
他不知道,我家的围墙有块石头松动了,只要打开它,我就能窥到外面。
窥到他。
窥到他在巷子口跟燕姨聊天,有时候在她那买一束花。
实际上燕姨哪进过什么花?火车站没人需要那种娇生惯养、朝生暮死的废物。
那不过火车站泥地里的野玫瑰,不知是哪年哪阵野风或野猫野狗带来的籽。
年复一年,吸着喧嚣、浓烟跟尾气,粗糙凌乱地长大。杆是脏的,叶是脏的,刺是脏的,连花儿也垂着头,一脸憔悴。
也就是他,会用干净的手,把这种破玩意儿好好地捧着,带回家插在糖水里。
浪费这种精力。
把垃圾当宝一样地护着,就只有他。
为垃圾怜惜、爱慕、心碎、痛不欲生、铤而走险、报仇雪恨……也就只有他。
垃圾一生,能得他照拂,夫复何求?
想到这儿,我又站起身。
想跟他说什么呢?
说不管他做了什么,我都不会觉得害怕。
或者说,当初没留下他,我其实也……
还是说,这回真的祝他前程似锦。希望他放下过去,好好享受未来的人生吧。
就此别过吧,再见。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很想回去看一眼。
无比强烈得……
很想再看他一眼。
就好像不做这事,余生都会睡不好觉似的。
我就这么一边胡思乱想着,走回到了车旁。
车窗关着,但我还是一眼就能看到了梁墨冬。
他正靠在椅背上,胳膊捂着肚子,闭着眼。
额头上淌着豆大的汗珠,苍白的嘴唇紧抿着,双唇交接的地方透着殷红,就像随时都能吐血。
我心里一惊,连忙拉开车门,推他叫道:“梁墨冬!”
一连叫了几声,他才吃力地张开了眼,我擦了擦他脸上的汗,问:“能动吗?到副驾驶,我送你去医院!”
他明显已经听不清我的话了,几乎没有回应。
我根本抱不动他,只好先退出来,打算从附近喊个人帮忙。
然而这会儿才现,车旁边已经围了点人。
车头前面躺着一个人,是上次讹六子那个老头儿。
听说他上次讹到了几万块钱,虽然没证据表明六子撞了他,他甚至没有伤,但六子为了仕途掏钱认了这个灾。
此时老头儿横卧在车头下,缩成一团,“哎呦、哎呦”得叫。
我关上车门,下了车,拉开后备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