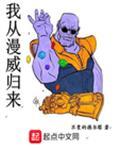笔趣小说>昨日重逢by半黄梅子雨 剧透 > 第74章(第1页)
第74章(第1页)
>
他熄灭烟头,简单一句:“跟我来。”推开门,笑着和保镖打了声招呼,道:“卡西酮用完了,我们得换个地方重新注射。”
沈煜清躲在角落里,保镖探头没看见,犹豫一瞬,道:“许先生稍安勿躁,我去通报宋先生。”
“你确定要在宋先生吃药的时候打扰他?”许敬若眉梢微抬,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保镖心里一寒,笔直得站在门厅,犹豫不决。
“刚刚你也听见了,宋先生说这里交给我处理。出什么事我单着,你怕什么?”
“这……”
许敬若凑近一步,目光从他的领带,扫到肩头徽章,最后停留在他的脸上,直直对视,充满压迫,“要是你打扰了宋先生,影响‘药物’吸收,你怕不怕宋先生送你下地狱啊。”
保镖也是新来的二十岁年轻小伙,刚从赌场出来,自是知道宋高远整人手段,被许敬若这么一唬,果真脸色复杂,点头应下。
“那麻烦了啊。”许敬若晃了晃空针管,针头落下两滴药水,保镖蓦地后退,跑远了。
“等下知道怎么出去吧?”许敬若关上门,朝角落扬了扬下巴。
“嗯。”沈煜清解开衣领前两颗扣子,勒紧领带,保持片刻,果真出现了一道的红痕。
“哟,你这自残方式挺熟练啊,不会是跟夏闻竹学的吧。”
“在芝加哥那两年,宋高远教的。”
沈煜清面无表情,手腕紧贴着金属手铐,来回转动,腕间青紫一片。
许敬若眸光凝了凝,想上前,又想起身后的监控,手背在身后,不再说话。
半刻钟后,四五个保镖从远处跑来,“许先生,车备好了,您带着沈先生出来吧。”
“好。”许敬若抓着沈煜清的后衣领,神情自若的走出来。
走廊的灯照在反光地板上,沈煜清眼稍微抬,不动声色地观察眼前人。
这几个年轻保镖,肩上都别上记录仪,是宋高远监视新人最常用的手段。
沈煜清呼吸停滞了一瞬,垂下眼眸,被人架着走进暗室里的电梯。
楼层缓缓下降,他的心也跟着下沉,“叮”地电梯停在负一楼,两旁的保镖按着他的肩,塞进黑色越野车。
车里仍有监视器,沈煜清半闭着眼,颓然的倒在座椅里,许敬若从副驾驶回头,眸光闪了一瞬,好似在说:“演得不错,真像注射了卡西酮。”
沈煜清眼神漠然,没有回应。
身边的小保镖正襟危坐,时不时低头看一眼肩上的记录仪。
沈煜清靠在窗户上,额头抵住冰凉的玻璃,车拐进隧道,路灯接连照进来,他最终没挡住内心深处的恐惧,想起遥远的芝加哥。
那时他刚和宋高远签约,肩上也带着监视器,帮宋高远打理赌场。
宋高远是个疑心病很重的商人,知道赌场是个染缸,灰色交易无时无刻地发生,让新来的手下进去犯罪,再带回身边,更安全。
宋高远带着他进入赌场,游轮行驶在密歇根湖上,周围满是保镖,远处飘来大麻刺鼻的味道,穿着比基尼的女人,走向他,递来一杯鸡尾酒。
干瘪的柠檬摆在酒杯上,橙黄色的液体上飘着白色粉末,沈煜清脸色苍白,那一刻他想逃,但汽笛声响,船发动,行驶在黑夜里,芝加哥的天际线越来越远,威利斯大厦隔着一层雾,飘摇不定。
沈煜清手背在身后,没接那杯酒,宋高远笑了笑,递上来一张照片,沈煜清瞳孔倏然瞪大,接过照片,坐上赌桌,签下合约。
宋高远要求他在赌场干半年,才准回到国内,和夏闻竹重逢。
染缸里什么人都有,血腥暴力无时无刻地发生,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很难坚持下来,沈煜清每每见到厮杀,都躲到甲板上,隔着灰扑扑玻璃,看赌徒红了眼,付不了账单,砍下半个胳膊,拿身体还债;看女人脱下裙子,用青春卖命。
鼻腔满是臭鱼烂虾的味道,沈煜清蹲下身,头埋进臂弯里,躲不掉,逃不开,心里默念,回国见夏闻竹,必须先渡过这一关。
狂风骤起,海浪肆虐,远处灯塔照不进这片角落,沈煜清强压住心底恶心,回到宿舍,翻出枕头下的照片,指尖摩挲毛边的相纸,弯起唇角,眼泪却“啪嗒”滴在照片,那人笑脸上。
十七岁的夏闻竹,坐在教室里,风吹过桌角的习题,他抬手压住书页,指尖落在盛夏的暖阳里,让人挪不开眼。
“咔嚓”耳边响起相机快门声,他偏过头,看向走廊,眼里含笑,朝对面的人挥了挥手。
沈煜清握相机的手一颤,又一声快门声响,定格这瞬间。
“你怎么没去新生典礼,在这偷拍我啊?”夏闻竹转着笔,歪头打量他。
“我…”沈煜清连连后退,不知说什么,本能想躲,但又舍不得。
这美好的夏天,他和夏闻竹只隔一扇门,心中雀跃,但不敢踏进教室,那种从孤儿院开始就烙印在骨骼里的自卑,让他一次次沉默。
沈煜清跑远了,夏闻竹没有追,卷子翻了一页,镜头模糊,十七不再,芝加哥的冬天很冷,彼此隔着十三小时时差。
那年,沈煜清听着牌九和骰子相互碰撞的声响入睡,梦里是没有勇气踏入的高三教室。夏闻竹头发染上暖黄的光晕,远远对他笑,笑到最后,沈煜清眼眶红了,看不清他的脸。
上帝惩罚他的懦弱,醒来,身边只剩芝加哥漫长的冬季。
如果再见不到夏闻竹,他会不会忘记自己?会不会结婚?夏闻竹的声音是什么样,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