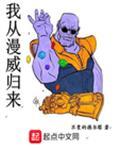笔趣小说>昨日重逢by半黄梅子雨 剧透 > 第41章(第1页)
第41章(第1页)
>
“沈煜清刚出生不久,学长去世,家里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了,他妈妈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想去婆家,婆家不认,回自己家,父母嫌她带着个拖油瓶,也不让回。那会象堡附近大学收的中国人不多,街对面中超生意不好做,沈煜清他妈妈一人打零工养不活他,何况她和学长也没培养多少年感情,最后受不了,离开了出租屋,回到了父母家,把沈煜清弃养在出租屋里。”
夏闻竹眉梢一挑,回头看他,眼眶通红,“这难道不犯法吗?”
“犯法?”司机抽烟的动作一顿,冷笑道:“学长被那群飞车党拖得血肉模糊,最后犯人一个抓住,你说弃养犯法?谁管啊?除了孤儿院,谁管沈煜清?”
身后响起车喇叭声,他抬高声音,回头看,路口堵车了,阳光下,黄色的车牌晃得眼睛疼,司机低头,默默把烟抽完。
异国他乡,很多事身不由己,他们当年想上诉太难了,没钱没人脉,最后把学长的骨灰火化送回国,都费了不少力气。
房东好心,把沈煜清领养的地址告诉司机,前两年他们相认,他才有机会才把学长过往讲给沈煜清听。
司机叹了口气,偏头看向身侧,说道:“夏同学,你太年轻了,还是先把眼泪擦擦。”
“我没哭。”夏闻竹倔强地举起袖子,擦了一把脸。
司机给他递了包纸,打开车门,“还想去哪里,我送你。”
“不了,回家。”夏闻竹坐上车,头埋在抱枕里,肩膀微微颤栗。
司机瞥了眼后视镜,指向窗外道:“夏同学啊,伦敦不只是切尔西和肯辛顿这两个繁华区。你回头看看象堡,那是我们当年待的地方,如今过去二十多年,原本的那栋公寓都拆了,改成公园。”
他眯起眼睛,像在说老电影台词,缓缓开口:“日子真不经过啊。”
夏闻竹抬头,吸了吸鼻子,脸上没有泪痕,司机舒了一口气,下一秒就听到他道:“大哥,他父母为什么要来伦敦,明明生活这么艰难了。”
“还能是啥,美国梦呗。”司机望着头顶飞过的鸽子,自嘲般笑了笑。
“刚到北京那会,身边人都想出国,时间久了,我们也想赶潮流。但当时竞争太激烈,我和学长都怕去不成美国,好在有个英国的学校和我们对接,读完那里的本科就能去美国读研。”
司机单手开车,又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道:“当时年轻,我俩心一横,就改了志愿,心想先出去再说,反正比大家挤破脑袋在朝阳区等美签强吧。”
夏闻竹闭了闭眼睛,车里的二手烟熏得眼睛疼。
“所以,他们的结局就是四散逃离,尸骨埋在异乡,还留一个孩子在世上,最后送进孤儿院?”
司机点头,没有说话。
“何必呢?”夏闻竹脸深埋在掌心里,想不通。
“那会年轻,只想着出来闯一闯,谁知道路这么难走。”
人总得犯错,所有的事尝试一遍,才会觉得开始的美好。
他们眼里的伦敦,不过是北京秋雨后,路上积水反射的乌托邦,倒过来看,不如家乡那条落满梧桐叶的老街。
夏闻竹靠回座椅里,盯着身侧空荡荡的座位,心脏怦怦跳动。
时间一去不复返,樱花落下的那天,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相遇倒计时,沈煜清被父亲带回家。
夏闻竹拍了拍沈煜清昨天坐过的座位,回头想想,他们之间的感情很简单,比起千禧年代的文艺片,他们没有什么感情纠葛,只不过是两小无猜,青春期的分开,又在温哥华重逢。
窗外风景不断倒退,车子停在公寓楼下,夏闻竹道了别,迈着沉重脚步上楼。
他心里想着事,这些年他和沈煜清之间,难道只是竹马情谊吗,青春期暗生情愫,是梦还是真实感受?
夏闻竹想不通,用力拍了拍后脑勺,如果把所有记忆追回来,会不会就能明白自己心意了?
他盘起腿,坐在窗台,往楼下看,心跳如鼓,脑海里只剩下沈煜清。
他一手托腮,盯着手里的翻盖手机,想给他打电话,听听他的声音,但又怕他在开会,叹了口气,收起手机。
公寓楼下有个陌生的路牌,两旁栽着熟悉的梧桐树,伦敦真的有好多梧桐树,就像n市一样。
夏闻竹眨了眨眼,忽然想起高中操场也栽着梧桐树。
大课间跑操,有时也能见到沈煜清的背影,当时他们不过隔着一群人,远远对视。
后来毕业,彼此天各一方,隔着十五小时的时差。
夏闻竹低头,下意识地在地板上画了一个爱心。
今天过分的心疼,之前过分的关注,还有未来想一直陪在沈煜清左右,明明都是喜欢他的征兆,但自己作为哥哥的身份摆在这,又能怎样。
从小到大,母亲都在说他是哥哥,哥哥对弟弟只能是亲情,越界一步,都是倒反天罡。
如果只说一两次还好,但日积月累,青涩感情,最终被深埋在心底。就像是司机之前说九十年代的北京,大家在一个学校,想着出国,耳濡目染,原本没有出国的打算,最终也登上了伦敦的飞机。
夏闻竹咬着下唇,擦掉地板上的爱心印。
况且,他也不知道沈煜清那边怎么想,虽然沈煜清青春期很依赖自己,但不代表那就是喜欢。
说不定沈煜清那会没安全感,家里又只有自己一人搭理他,沈煜清不找他找谁呢,如果多一个人,说不定他就不黏着自己了。
夏闻竹从不做没把握的事,他拍了拍脸颊,苦恼了好久,终于想明白,如今他只要维持现状,用哥哥的身份陪在他身边,绝不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