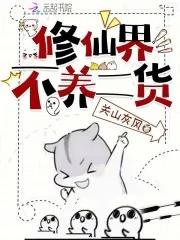笔趣小说>穿越后我被迫破案了 > 第230頁(第1页)
第230頁(第1页)
她扭過頭想看一眼租客的模樣,卻與對方驀然投向自己的目光對個正著。
手裡的畫板「哐啷」一聲掉在地上,呼吸在這一刻完全停滯,邱靜歲寧願相信眼前看到的是幻覺,因為她的大腦根本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
那「租客」一步步走過來,邱靜歲覺得他踩的不是路,是自己的血脈心臟。
他稍稍彎腰把落在她腳邊的畫板拿起來:「姑娘,你的東西掉了。」
一種荒謬感襲上心頭,邱靜歲一時之間竟然分不清這是夢境還是現實。如果是夢境,為什麼他不認識自己?如果是現實,那世界上怎麼會有兩個長得一模一樣的人?
「你……」對方好像是第一次見她的模樣,邱靜歲干站了半天,心情複雜地問,「你叫什麼名字?」
明明因為撿畫板所以站的距離和她過於靠近,但是對方直起身後,仍然沒有退後一步的意思。
那人微微頷,十分有禮地回答道:「在下姓6,名行之。敢問姑娘名姓?」
第138章
怒意像是憑空出現的,但是卻很快占據了邱靜歲的心房,她抖著唇說了幾聲「好」,而後道:「我姓郝,叫綰蔴。」
說完她開了院鎖,用手臂推開院門,看也不看他,徑直回了屋。
被閃在門口的6司懷把她說的名字在口中念了兩遍,垂下眼,想笑又笑不出來。
回到屋裡,邱靜歲把東西往桌上一扔,叉著腰站在地下走來走去,眼睛瞪的溜圓,稍微冷靜下來後,她開始探究自己生氣的原因。
在其位不謀其政,一國之君肆意妄為是為一。
有妻有子,卻來這裡擺明了要招惹她,是其二。
好吧,最讓她生氣的是第二條。
他把自己當成什麼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她想逃,只有逃到其他國家去。可是陌生的語言文化習慣不是任何人都能輕易適應的,起碼邱靜歲不想離開。
晾著他吧,他的性格加上這幾年浸淫權力養成的習慣,一定受不了她的冷臉,想必沒多久就會回去了。
一個帝王的權力有多大?任何人任何東西,只要他想要,軟的不行還可以來硬的。可她下意識地忽略了這一點,或者說,她還是好多年前的慣性思維——6司懷是不會勉強她的。
為了避免和6司懷見面糾纏,邱靜歲出門更加頻繁,早晨天不亮就背著畫板往城外跑,一直到天擦黑才肯回家。
一連三天下來,邱靜歲都沒有再見過6司懷的面,如果不是晚上能聽見那邊院子裡傳來打水燒柴的動靜,她還以為對方已經走了。
這樣的狀態非但沒有讓她覺得舒服,反而更加彆扭,心裡像有一股邪火,想發卻發不出來。
一天早晨她睡了會兒懶覺,出門的時間比往常稍微晚了一刻鐘,結果正撞上6司懷也出門來。
他拿著幾貫錢,看見她,停住腳步,朝她點點頭,道:「我見郝姑娘總是這麼早出門,注意路上小心,早些回來。」
邱靜歲的無名火又上來了,她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一句話也不搭理,掉頭就走。
走出去一段路後,她做賊一般地回頭偷看,6司懷沒有跟上來,卻是和她背向而行,往縣裡北市的方向去了。
要去幹什麼?邱靜歲不由煩躁,整整一天她都沒能完全靜下心來。
不想在外面乾耗時間,邱靜歲提前回了家,準備拿上之前畫的存貨去書齋看看有沒有銷路。
書齋的柳掌柜見她上門,熱情地招呼了一聲,瀏覽完她帶來的畫作後,委婉地問:「前幾年你畫的宴請圖賣的很好,怎麼不再畫了?」
那都是舊日腦子裡還殘留著京城繁華的印記時畫的,如今要她一個普通百姓如何再動筆?
「畫不出來了。」她照實說。
柳掌柜顯然不信,卻沒有戳破,又問:「去年那對門神畫的也好,神荼鬱壘活靈活現的,今年年底還再畫吧?」
「畫,不過也畫不多。」邱靜歲問,「手上這些,是不是沒有入眼的?」
「幾幅小孩子的還可以留一留,其他這些……我說大妹子你做什麼總是畫這些小老百姓,看起來缺了點喜慶,平常人家哪裡愛掛這個。」
要麼陽春白雪,要麼下里巴人,但是邱靜歲的畫卻有些特立獨行,總之並不太受市場歡迎。
她也不著惱,把柳掌柜要的畫留下,出門在街上空轉了轉,沒有看見6司懷的身影,只得懷著也不知道是個什麼樣的心情往家走。
到胡同口,邱靜歲一眼看見6司懷正扛著一塊門板往院子裡運。
是可忍孰不可忍,有沒有一點租客的自覺了?邱靜歲三步並作兩步趕上來,肅目問:「不要隨便改動,這家主人回來還要自己住呢。」
6司懷把肩上的門板放下豎在門口,回身看著她,語氣是溫溫的:「西屋門板漏風,我拿它擋一擋,不會亂動的。」
曾幾何時,他也經常用這樣的語氣同她細細地說話。他的聲音簡直比任何安眠的香料都要管用,邱靜歲數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在這樣的聲音中陷入沉睡。
恍然間,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他們還是恩愛夫妻的年月。
「你還要裝到什麼時候?」這樣的問話邱靜歲差點脫口而出,不過最後她只是道,「走的時候把東西都清走。」
「好。」
小貼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1t;)
&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