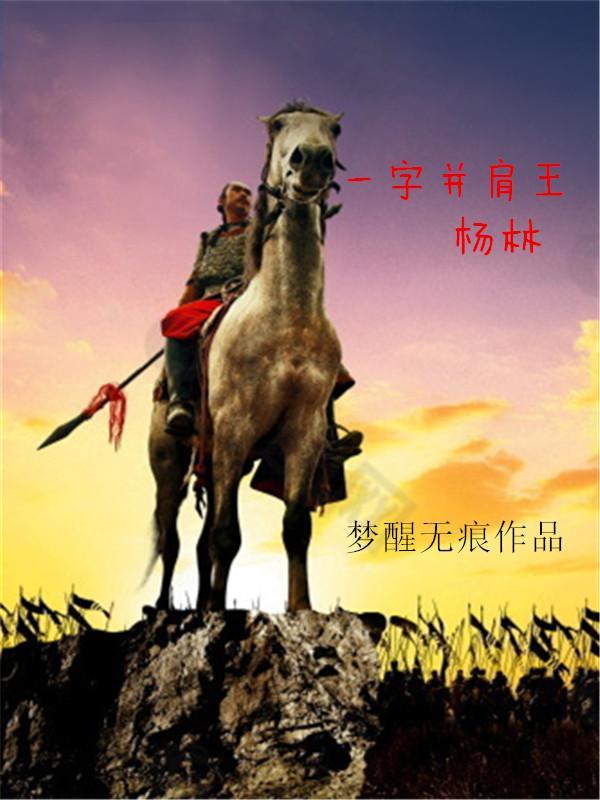笔趣小说>多伦多有条羊街 讲什么 > 第88页(第1页)
第88页(第1页)
一进车,她的酒劲就又上来了,眯着眼靠在椅背上,听见他说了句:“我得先去加个油,不然送你回家,我再回家可能不够跑的。”
“那就直接去你家。”她舌头不太利索。
“啊?”他不确定他听到的话。
“下这么大雨,你还两头折腾,不累啊?我还能把你吃了?”她不耐烦地打了个呵欠,有点不满他的磨叽似的。
他磨叽了一会儿,又磨叽了一会儿,终于一踩油门,车子“呜”地一下驶了出去。
翌日,她是在窗外大街上的一阵摩托的引擎声响中醒来的。
她发现自己正叉手舞脚地躺在一张陌生的大床上,枕头被子上满是一股汰渍洗衣液的香味,这味道她可太熟悉了。
她身边只有一个人用这款洗衣液——安童。和他相处久了,她知道了“汰渍”的这款洗衣液的味道叫“清新的风”。这股“清新的风”使他没有男孩子身上惯有的一股懊糟气,还赋予了他一点纯情处男的芬芳。
她很快便想起昨晚,他把她开回了家——他的家,也是个共管公寓。
在密西沙加。
她知道这是密西沙加,不光因为她一直知道他住在这里,也是因为昨晚她一个盹醒过来,刚巧捕捉到车窗外一闪而过的密西沙加的地标建筑——“梦露楼”。就是两幢模仿梦露的腰身建造的公寓,她还特地仰视了一下“梦露”,发现那两幢楼并不像梦露那著名的中下围,倒更像可乐瓶,其中一只“瓶”还被踩变形了——就是收破烂的下死劲往脚底一踩后的那种变形。
还好,安童不住那两幢楼。
她最后的记忆就是主人好心让她换上干净衣服,还慷慨地让她睡床,自己抱了枕头被子出去了,大概是去隔壁房间睡了
醒来没一会儿,她就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
安童刚刚出去了?有室友?昨晚又晕又困,只约莫知道他有两个房间,不知有无室友。
不等她闹明白,开门的人就进来了,还有塑料袋窸窸窣窣的声音。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从床上起来,打开卧室的门出去了,不管是室友还是安童,都得打个招呼致个意。
厨房里,有个中等身高的中年女人忙活的背影。等等,这个背影怎么这么熟?那背影听到响动,也转过了脸来,陈飒吓得一声“哇”——
廖静正瞠目结舌地瞪着她。
生在福中不知福
陈飒从她的眼神里读出了一股杀气。
双方正大眼觑小眼地僵着,又有钥匙开门的声音,两个人、四只眼齐齐瞪向门口——安童气喘吁吁地从屋外闯了进来,气急败坏地冲廖静喊了一嗓子:“妈,你咋自己上来了呢?不跟你说我有朋友在呢吗?”
他在次卧睡了一宿,起床时看陈飒没醒,冰箱里一点早餐的料都没有,就晃荡着去楼下二十四小时不打烊的连锁超市rabba,买点鸡蛋牛奶面包培根啥的。
进了超市,正在逐个检查一盒鸡蛋是不是都是无缝蛋,就接到了妈的电话:“童童,妈给你把下星期的午饭给你做好了,给你送过来,啊?”
他差点砸了手里的一盒蛋:“你先别进去,我有朋友在我家。”
“妈已经到门口了,给你搁厨房就走。”妈有他公寓的钥匙呢。
他挂了电话,扔了鸡蛋,拿出马拉松冲刺的水准往家奔,谁承想还是迟了一步。
妈对他和陈飒走得近一直忧心忡忡的,明里暗里地警告他不要跟这种油里油气的女孩来往——看她那年纪,说话穿衣没羞没皮的样子,还有点女孩的矜持样吗?
他给妈解释过,陈飒是免费帮他指导职业方向的朋友,还给他引荐谁谁谁。妈就不好说什么了,可是昨晚在游艇上,他俩一道走,下着大雨,别人没留心,妈留心了。
今早就是来突击检查的,没想到她最怕印证的事,得到了印证。
不等她想出什么应对方案,陈飒就率先打破了僵局:“我要回家了。”
“我开车送你吧。”安童忙道。
“不用,我坐地铁。”
“我们这一带没地铁。”
“那我‘呜呗’。”
陈飒的眼睛四下里找了一圈,然后落在客厅撑起的干衣架上的碎花裙上——没想到东北小伙儿这么细心地把她的湿衣服平摊着晾了起来,还捋得褶是褶,边是边的。同样进入她的眼帘的还有干净整洁的客厅。
她赶紧过去把裙子扯到手里,慌不迭地进了主卧的卫生间,迅速换了衣服。
“还是我送你吧?”她在门口换鞋的时候,安童追出来。
“不用。”她小声而坚决。
她在回家的车上百爪挠心地纠结着。
她不常纠结,一纠结就把好多原先不通的事儿弄明白了:比如,为什么每回她一说廖静的坏话——她可没少说,安童就顾左右而言他的。
还比如,为什么廖静一看到她和安童在一块儿,就苦大仇深的。
远的不说,就说昨晚在游艇上,她为什么突然提议大家用母语唱歌?就是天上滚雷以后,大伙儿都跑开了,一张桌子上就剩了她和安童,人家当妈的看着不乐意了呗。所以一改往日的冷淡做派,提议大家唱歌,然后顺理成章地冲陈飒和安童说:“你们也过来吧。”好结束他俩的独处
这会儿,她把这些纠结告诉了兰珍,然后忧心:“她一直不待见我,以后不会给我穿小鞋吧?”
兰珍摇摇头:“我觉得她不会。毕竟,你们的机构和我们一样,都是有工会的。她把自己的儿子偷偷招进去,是赤裸裸的nepotis(裙带关系),如果她职场霸凌,你完全可以去hr或工会举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