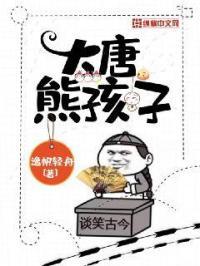笔趣小说>山海谣舞蹈 > 第 7 章(第2页)
第 7 章(第2页)
周围坐着的另几位长老悻悻摸着鼻子,也没再说什么,对此几乎习以为常。
楚明姣足尖微点,在虚空中踏着无形的阶梯一步步走上了那道巨大的台子,最后与楚行云面对面站着,两人中间离得不远,只差不多十几步的距离,她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位比她小不了几岁的弟弟鼻尖沁出的汗珠,还有他眼皮上褶皱不经然的痉挛颤动。
“还剩最后一道?”楚明姣随意地瞥了瞥台子上那道唯一存留的分身镜像,很自然地下了决定:“这个不作数了,和我打吧。”
楚行云不由皱眉:“二姐姐,这……恐怕不合族老们定下的规矩。”
“不是一直想要楚家少家主之位?”楚明姣垂下眼,踩着自己的影子,语气没什么波澜,平静地好像在和人谈论今天的天气:“赢过我,少家主之位,你拿去。”
楚行云左右为难。
他没有比楚明姣小几岁,这位说是姐姐,其实在他眼里,更是个金尊玉贵,受不得半分委屈的姑娘,和妹妹差不多呢。
当然这样可能多少有些看轻人,当年能和楚南浔,楚明姣混在一起嘻嘻哈哈打闹的,全是山海界下任掌权者这样的人物,而即便是在这样的圈子里,楚明姣依旧混得风生水起,不比楚南浔差。
这足够说明一些事情。楚明姣并不简单,可转念一想,能被神主迎娶回潮澜河的姑娘,除了天生的美貌外,自然要有点不同凡响之处。
事实上,很少有人见楚明姣出手。
即便这一年一次的九月九登天门,她每次来搞破坏,也只仅限于用圣蝶的力量偷天换地,往楚滕荣那三道分身镜像中注入如汪洋般浩瀚的灵力,让他无法再往前踏一步。
像今天这样,像是已经厌倦了这种每年一次的游戏,想要彻底做个了结的状态,楚行云第一次见。
但……如果不答应,她这搅破天也没人管的架势,连父亲都拿她没办法。
潮澜河那位,明里暗里的,给了她很多特权,听族中长老们红脖子赤眼睛总结出来的那个意思,就是楚家闹塌了都行,楚明姣反正不能出丁点事。
所以她今日终于肯松口,对他而言,其实是件好事。
反正。
怎么都比这么一年年耗下去好。
“好。”楚行云也不拖泥带水的拖沓,他整了整衣袖,调理呼吸,再把碍事的辫子重挽上去,从袖口中反手抽出把冷光凛凛的乌骨弓,右手三根手指同时用力,将锋芒毕露的箭簇对准楚明姣眉心,郑重其事道:“刀剑无眼,若有冒犯之处,请二姐姐原谅。”
楚明姣无所谓地颔,一个巨大的防御阵从她脚下散开,将台上与台下分开,以免后面打起来伤及无辜。
有一点楚行云说得没错,她已经厌倦这个年复一年,如小孩子般玩笑打闹的游戏了。
她心里憋着一团巨大的火气。……
她心里憋着一团巨大的火气。
不泄出来,她整个人都要由里而外地炸开了。
楚家嫡系这一脉天赋都不差,即便不如死去的楚南浔,但十三年过去,笨鸟都知道先飞,楚行云奋起直追,如今也差不了多少。
楚行云连出三箭,离弦之箭震得乌骨弓都嗡鸣着震颤起来,他虎口麻,冷静地看着它们直地朝着楚明姣贯穿过去,那种惊人的力道暴烈挤压着,似乎连空气都化为了潮湿的泥藻,畏缩着臣服。
看得出来,他想战决。
箭矢飞掠到眼前,度快到极致,带起的风声如同尖啸,陀螺打转般重重钉进楚明姣的耳朵里。
她脑子里的本能告诉自己,化解这三箭其实并不费力,她手上有圣蝶,这是人人都想要的好东西,灵力无穷尽,她可以用这个抵挡一部分攻势,就像那天阻挡祖祠里的禁制反噬一样,最后再用些技巧把这三箭化了——这都不是问题,说不定还能把这箭簇留下来。
听说这是楚滕荣亲自给选的灵物,还挺值钱。
接着呢,接着轮到她出手了,她应该克制一点,这么多人看着呢,她不能对自己的弟弟太狠,怎么说都是同父异母,身体里流着一半相同的血呢,把他轰下去就行了。
就像之前每一次,她懒得跟他们计较。
但是凭什么呢?
凭什么呢!
一股巨大的悲伤与不甘突然席卷四肢百骸,在她的身体里汇聚成了难以止歇的风暴,须臾间,什么隐忍,什么小惩大诫,什么不予计较,连同理智一起,全都被这股风暴碾得粉碎。
天地间风云变色。
确实是一刹那间,原本还高悬在头顶上的太阳温吞吞藏进了突然积厚的云层里,那云的颜色深得像是泼了墨,又湿得能拧出水来,一柄格外锋利的小剑从云中显现出来。
它像是缩小了,看起来更像是匕,相比于楚明姣事事精致讲究的风格,这剑很素净,朴实无华,此刻引人注目的原因也简单。
被寒光覆盖的刃边太过锋利,几乎给人种能切割灵魂的危险感。
这个时候,那三道箭矢已经快要隐入楚明姣额心,而后面,楚行云抿着唇,接连搭弓,上箭,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又补了几箭。无法成为少家主,就意味着无法进楚家祖祠接受最核心的传承,已经十三年过去,他本就比那些人差一点,经不起时间拖耗了。
他真的是需要这个位置。
再说,楚南浔死了,楚明姣性格太阴晴不定,志不在此,少家主之位,本就该落在他头上——这是连楚滕荣都默认了的事。
这接连六七支箭矢,足以将楚明姣困住,伤也不怎么能伤得了她,她身上有不少潮澜河的灵物庇护。
他都已经算好了可能会遇到些什么情形,唯独没想到会看到眼前这一幕。
那柄小剑绝不可能是某种灵物。
灵物上不可能有那样磅礴凛厉,且任人差遣的剑意,那只可能是自己的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