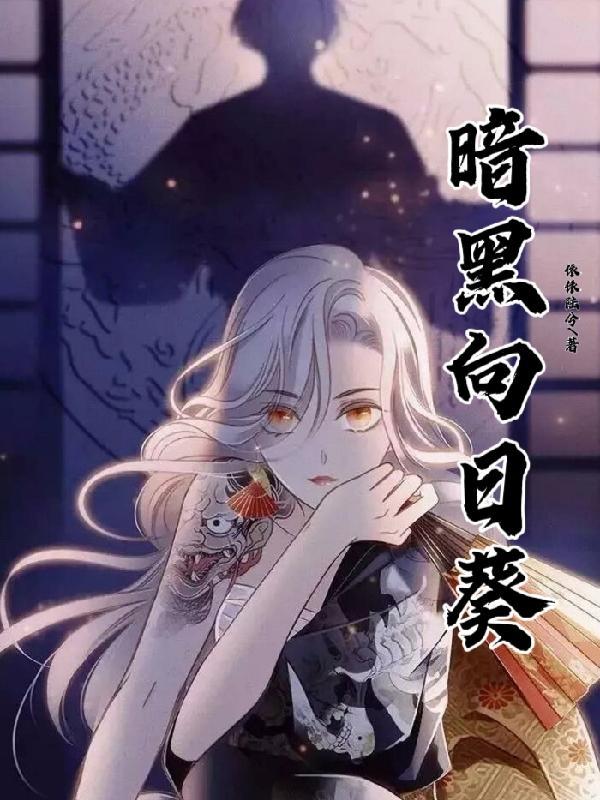笔趣小说>我回科场捞人上岸科举笔趣阁 > 第20章(第3页)
第20章(第3页)
原疏夹在中间,苦大仇深闷下一壶冷茶,破罐子破摔道,“得,反正您二位也这么处了十来年,就这么着吧。”
散席后,李玉果不其然又没了人影。
原疏怒其不争,“这人真是,旁人几句闲言碎语还当真了!天天躲我们跟躲瘟神似的。”
明着是骂,但顾悄知道,原疏这是反向输出,替李玉说好话呢。
休宁县里,到哪李玉都要被指上一句贱民。
低调行事,是他惯用的生存之道,尤其在方白鹿公然奚落顾悄交友不慎后,他更是主动避讳。
顾悄哼了一哼,“原七,差不多得了啊,我是那种不明事理、小肚鸡肠的人吗?”
原疏嘿嘿傻笑,片刻后叹息道,“近日来,琰之心细了许多,我是怕李玉那锯嘴的葫芦,闷头行事,平白惹得你们生出嫌隙。”
顾悄慢了半步,盯着原疏后脑,心道他与原身行事,差异还是过于明显。
正当他暗自警醒,日后更要谨小慎微,却被原疏接下来的话,整得破了功。
“但是吧,原来的你万事不过心,看似好处,可我总觉得,你压根没将我们放在心上;现在的你,事儿事儿的,管得还宽,但看着你为我们操心,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顾悄额头青筋狂跳,事儿事儿的?小伙子,你很可以嘛!
他嘴角扬起一抹笑,对着忘乎所以的原疏,温柔道,“子野,既然你这样开心,我这里有件事要你出力,你定然不会推拒。”
原疏的笑,僵在嘴角,一张脸皱在一处,如寒冬腊月里抱在枝头的干菊花,瑟瑟抖。
他咽了咽口水,“什……什么事?”
顾悄扬了扬手里的宝钞,“当然是替黄五找说客,我想,你姐夫就很合适,能把你弄进顾氏族学,再弄一个黄五肯定不在话下。”
原疏瞬间垮下批脸。
跟顾悦开口讨人情,不如给他一刀痛快。
愣了片刻,原疏一把抱住顾悄的腰,“顾大哥,顾夫子,我跟他向来不对付,求求你高抬贵手吧。”
如此不顾风仪地当街耍赖,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啧,难怪顾三处处护着原家这破落户,没想到你们二人竟是这般关系,真是斯文扫地、不堪入目!”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打断二人嬉闹。
顾悄转头,就见到内舍几个学子,脸色不善地挡在他们跟前。
听这声音,可不就是族学里骂他们“废柴”不成,反倒被顾悄呛了一鼻子灰的家伙!
还真是冤家路窄。
至于“这般关系”是哪般,那就淫者见淫了。
本朝男风盛行,不仅馆院众多,不少世家子弟背地里亦有勾搭,一个圈子里混的,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反正原疏几乎是秒懂了。
“朱庭樟,你不要太过分!”他烫手般松开顾悄的腰,老母鸡护崽般拦在他跟前。
朱庭樟已是及冠年纪,生得鼻挺眉阔,唯有一双眼狭长有光,鼻梁上若再架个金丝镜框,便活脱脱一个日系校园漫里的风纪组小组长了。
他同原疏一样,与顾家都是姻亲,倒也说不上谁比谁高贵,唯一的差别,便是朱樟庭家族争气,他在顾家向来被奉为上宾。
这番他显然不怀好意,张口便带着尖刺,“不知‘顾夫子’跟原小七,究竟谁在上头,谁在下头?我瞧着这阵势,倒更像是原七欺师灭祖啊?还是说……‘顾夫子’的束脩本就是这般收得?以皮肉来偿?”
这便是拿上次听的墙角说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