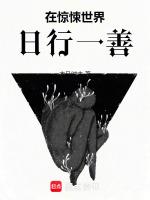笔趣小说>大佬穿进虐文后七千折戏 > 第七十八章 初一十五(第1页)
第七十八章 初一十五(第1页)
姜彦缨给自己什么了并不重要,裴筠筠想,对元隽而言,重要的是,姜彦缨这东西,是替谁给的。
他人已经站在这了,连姜彦缨三个字都道出来了,她稍加冷静之后,一想便知,自己赴宴时敷衍不过去的,非得拿出个真章程不可。
“没什么大不了的呀,”她不情不愿的将信拿出来,“就……转交了太子的一封信而已。”
“‘而已’?”
夜色昏黑,王爷的脸色更黑。他过去一把将信夺过来,捎带着还瞪了她一眼。
裴筠筠伸伸手,想拦不敢拦,眼看着元隽拆了信函径自看起来,心里七上八下的开始打鼓。
元隽看看信,看看她,神色晦暗不明。
“你跟他……”他停顿须臾,似是在寻找恰当措辞一般,最后问道:“曾说过些什么?”
“什么?”裴筠筠这时甚为后悔没有在外头将信看了。因着实在不知元殊究竟都写了些什么,她接着装傻的功夫极快的思忖一番,最终决定铤而走险。
她道:“也没什么,您也知道的,之前我吃了太子妃不少的亏,我又素来是个记仇的人,哪好意思不报复报复呢?……是以,离京之前,我曾给太子写了封信,好生编排了一番太子妃,全当小惩大诫咯……”
她这番铤而走险,实则倒也算得上实话实说。
在给元殊的信中,除却寒暄客套之言,她真正表明的,只有一个意思——
大雍国破后,自称等天嫡女、
类阳帝姬的当今太子妃,其真实身份,本是前朝天平帝同冯淑妃之女、当今皇后的亲外甥女,当年号称自焚殉国的芳仪帝姬,嬴稚。
此外,并无他话。
而就只是这一番话,太子若不信,落在她身上的便是滔天大罪。
出乎她意料的是,元隽听完她这番话,却没有问她究竟是如何编排太子妃的。
这便让她心头愈发惶恐了。
而更让她的惶恐,却还在元隽接下来一番不容置喙的话里。
“以后不准再背着我同元殊往来,听到没有?”
他目光郑重,态度更是前所未有的严肃,裴筠筠看在眼里,越发好奇那信中的内容了。
“为什么呀?”心里如何慌张另说,她面上却还是一味的镇定,甚至还有精神天真的眨眨眼睛,“他是太子,我一奴婢,他若非要与奴婢往来,我还能推拒不成?我哪来的胆子哟!”
“我给胆子。”
元隽掷地有声。
裴筠筠一愣。
顿了顿,他接着道:“说了不准就是不准,你不准主动招惹他,他若非要与你往来,你就给我胆大包天的拒绝了,责任只管往我身上推。”
缓过那股诧然,她轻笑道:“怎么推?说您不让我同他说话?”
她本是带了些打趣意味的随口一言,不料元隽闻言,却极是认真的点了下头:“不仅不让你同他说话,任何的私相授受,我都不准。这话是我说的,你只管原话给他。”
她与他对视片刻,眼里的玩
笑之意渐渐收敛了许多,偷眼往他手中那张纸上瞥了一眼,忖度少顷,试探着说道:“那……我也不能不明不白的就应了这得罪人的事儿,您总得给我个理由罢?”
说罢,她目光忐忑的把他望着,深追起来,却是连她自己都不知是想听一个什么样的理由。
“你想听什么理由?”他问,“我吃醋,我嫉妒,还是我害怕?”
她被这一连串直白的用词震了一震,张开嘴还没来得及发声,就见他朝自己逼近一步,双手钳紧她的双臂,定定的望着她道:“裴筠筠,你听好了,我就是吃醋,就是嫉妒,就是害怕。这理由若是不够,本王便拿王位来压你,你一时一刻是我的人,就不准做任何让我心神不宁的事,这是你身为婢女的本分。”
裴筠筠呆呆的看着他,半天没找到自己的声音。
烛火实在太昏暗了。她想。
还……挺想离他再近一点的。她又想。
想着想着,她默默吞了口口水。
寂静之中的吞咽声格外清晰,元隽这时候方才觉出两人的距离,以及这暧昧过了的姿势,顿觉心上一热,连忙遮掩着松开了她,背过身不再看她。
裴筠筠觉得,她的世子,脸一定又红了。
她叹了口气,嘴角不觉显露出一个弧度,心里倒是瞬间多了许多的勇气。
凑过去小心的牵起他的衣袖一扯,她声音轻软的问:“我……我能看看,他信上写什么了吗?”
话音落
地,便见元隽背在身后的手倏然一攥,那信纸便跟着团成了一团。
这就是不想给看了。裴筠筠发愁的垮下脸来,盯着他的背影,心里怨他小气。
“您这样……”
她本想说,您这样做不觉得无礼吗?可话还没说完,便被元隽给打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