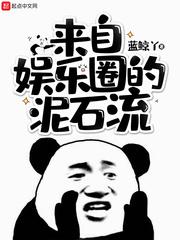笔趣小说>拥抱地球头像 > 第45頁(第1页)
第45頁(第1页)
「還記得我跟你說過的,我十七歲時候在一起訓練的那個滑雙板的中國朋友嗎。」池羽剛剛起了個頭,高逸已經知道了他說的是誰。池羽滑雪的運動員朋友很多,可這麼多年被他反覆提起,掛在嘴邊停在心口的只有一個名字。
在班夫的時候,池羽酒後跟他坦白過,而他自己也查過當年的聞。池羽載著他去參加比賽的夜路上出車禍,梁熠川當場死亡,池羽也受了重傷,不得不休賽兩年。梁熠川,梁牧也。姓氏不會說謊。高逸瞬間就明白了故事始末。
「你……是怎麼知道的?世界上姓梁的人那麼多。」
「他倆的聲音很像。我當年其實見過他一面,在大街上,那個時候……看得不太清楚。熠川說過,他哥哥是個攝影師;牧也也說過,他弟弟是雙板運動員……總之,錯不了。」池羽那邊頓了頓,是鋼銼磨刃的嘶啦啦的聲音,「我倒巴不得是我搞錯了。」
還有生日。梁牧也這幾年明顯是不過生日的,所以程洋才會是那種表情。就連他本人,最開始的反應也是驚訝、詫異,而不是欣喜。而自己,是他所經歷的一切痛苦的始作俑者。
不但如此,他還往他傷口上撒鹽。那天生日蛋糕梁牧也自己根本沒怎麼吃,他都看在眼裡。至於許願和切蛋糕,估計是不想讓自己太難堪罷了。
高逸嘆了口氣。
「唉,既然你都這麼說了,那我也不得不說勸你一句。」
池羽耐心道:「逸哥你說。」
高逸沒長篇大論地講道理,就簡單一句話:「池羽,你得告訴他啊。」
他以為比賽的重壓絲毫不會影響到池羽,這人可是遇到大賽即興奮型選手。可那個人承受的也不僅僅是比賽的壓力。
池羽那邊又沉默了挺久,他說:「嗯,我知道。」
「我知道你很難做,你跟他現在關係……」高逸咽了口口水,斟酌著措辭,「這麼近了,算是朋友。但是拖著,也不是個辦法。」
池羽的修刃聲停下來,然後,高逸聽見他說:「我知道。我比完賽,就告訴他。」
被他這麼一說,高逸八卦的心情也沒有了。
「逸哥,麻煩你,明天見到他,別跟他說。我……」
「明白,」高逸自然懂得,「你的事,我讓你自己告訴他。你放心。先別想這個了,該比賽比賽,想想你的路線,那個72o,做出來得多帥啊,是吧。」
池羽苦笑了一下,說:「說實話,這兩天想這個比想路線要多。」
他免不了去想,如果梁熠川還在,他還會和他滑「抄近道」小樹林。池羽在遇到他之前,沒有跟雙板滑得好的朋友一起滑過,遇到他以後,有一半的時間都在道外滑他的分離板。他把分離板用到了淋漓盡致,甚至引來了製造商青睞的目光,在他們下一雪季的產品宣傳視頻裡面出鏡了一個小片段,拿到了作為單板運動員的人生第一筆廣告收入。
池羽在收到支票的當天,就把那筆收入和梁熠川對半分了。梁熠川當時想瞞著他爸買車,零用錢是能省則省,都放在一個哆啦a夢存錢罐裡面。直到出事那天,池羽都知道罐子裡的餘額。
梁熠川其實很少和外人講起和他哥的故事。大概年輕的兄弟間總存在一種難以嚴明的競爭關係。始於青春期的荷爾蒙,後來又演變成關乎事業的自尊心。
時至今日,池羽也知道了為什麼。梁牧也自由生長成今天這個樣子,頂天立地,來去瀟灑。他的成功投下一片影子,而梁熠川在他的影子裡長大。他總是憋著一股勁兒,想比哥哥做得更好。換做任何人,估計也會如此。
可梁熠川每每提起他來,說我哥的項目,我哥去哪個山里拍片子,我哥說過等我滑得好了,就跟我一起去世界上最高的山上滑雪,驕傲之情溢於言表。池羽對他只有隻言片語的了解,無異於霧裡看花,站在這影子裡面,仰頭看一棵參天大樹。
如果梁熠川還在,如果他沒有答應對方趕赴那一場比賽,現在他也已經二十歲了。爭強好勝的青春期一過,他應該會更加願意和他哥哥一起玩。他也肯定會拉著梁牧也,介紹給在座所有的人。而他和梁牧也,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相識。也許是在加拿大,也許是國內的大山上。
若有個按鈕可以讓他倆之間一切清零,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按下。只是,現實不是虛擬遊戲,更不是訓練場。他練習多少次,也無法換回重來的機會。
*
等梁牧也開回了自己家,才打開手機接收消息。
鄭成嶺給他發了下周的初步踩點和訓練計劃,問他哪天要過來拍,他好安排購置合適的設備。他們平時攀爬訓練,基本不怎麼用靜力繩,只用動力繩,所以靜力繩需要買多少米,也全看攝影師安排。
梁牧也多了個心,打了個電話給他,先是確認了下禮拜的具體安排。
等確認好工作以後,他又開口問他:「鄭總,我問個事兒,你也幫我打聽打聽。」
鄭成嶺為人爽快,早就跟他稱兄道弟,便說:「別鄭總鄭總的了,叫老鄭就行。什麼事兒,你儘管說,幫得上忙的我當然幫啊。」
梁牧也笑著謝過他,這才開口問道:「邁中國……有沒有想過贊助滑雪運動員。」
「我知道在美國是有,在中國目前還沒有。我們最近五六年才開始做服裝嘛,你也知道。如果有合適的人選,當然可以考慮。我甚至可以幫你向總部提一下。你說的滑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