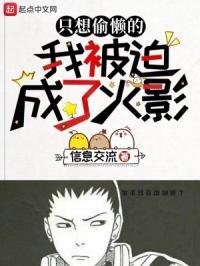笔趣小说>丫丫百科 > 第75章 至574页(第1页)
第75章 至574页(第1页)
不由分说,她便一手牵着一个把她俩往家里拽,木桶也不要了。
房子虽然破旧,木桌椅也没了光泽,杂乱的物件倒是被收拾的井井有条,燃烧的烟气中夹带着泥土的湿气弥漫在空气中。
刚跨进门的方姨就朝里面大声喊叫起来:“你们快出来看看谁来这里啦。”伴随着‘这时候还能有谁来咱这里’的嘟囔声,傅二娃一脸狐疑的从后院里走了出来,在魔法般地瞬间他就像泥塑一样一动不动的被定格在了那里,惊讶的表情难以述表,然后又猛然抬起了他仅留下来的那条胳膊有力的在大腿上拍了一下才出一声:“我的个天,夜个儿还梦见……,”他中止了后话,激动的指了指方姨,竟然说不出话了。
阿芳赶紧迈开双腿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说:“可苦了你。”如果不是在这样的场合相见,她和他的手恐怕是永远也碰不到一起的。
经过短暂的寒暄之后,阿芳没见到儿子便向方姨问道:“两个孩子在这儿别调皮吧?”方姨马上就说:“不调皮,这两个孩子真的很不错,你们聊着,我这就去把他俩叫过来。”
东平这时也站起身来对着二娃说:“怎么没见契柯夫,来这里也不给我去个电报。”然后就指向阿芳说:“大嫂可是一直在念叨着他。”痛苦与纠结使傅二娃不忍心在刚一见面就将满腹的苦涩倾倒出来,便支支吾吾的说:“他…他和我都了,了好几份,这样吧,我给你们看看这个。”说着就从香案下面的一个小木匣子里拿出了几张黄的纸片交到了东平手上说:“你看看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张不规则的小纸条被他随手丢弃在了桌面上,阿芳将它拿了过来,见是张强的字迹就仔细的辨认起来,之后就想再证实一下是,还是不是:“傅师傅,这上面的地址是写给谁的?”二娃一听就愣住了:“这不是你家的地址吗?”“哦,瞧我这眼,迷迷糊糊的也不好使了。”她的完美搪塞还没有得到的窃喜来的更加痛快:这正是她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
这时方姨已经带着两个孩子和一位老人一起拥进了堂室,两个如泥猴子一样的孩子见到了母亲自然也就依偎了过去,只有恒昌多了份腼腆,阿芳顺势在将两个孩子揽在怀里的同时也将那个碎纸头攥在了手心里。
分分钟的别子伤黏过后,刚才的话题仍在继续:“可我们连一份也没有收到呀!”东平说。
方姨瞅见二娃很久没再有过的脸色,还以为他们刚才已经说到过契柯夫的事,鼻子一酸,眼睛也就跟着浑浊起来,她用略带宽慰的口气对二娃说:“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你就不要再难为自己了,”末了又说了一句:“我去烧水,”之后就捂住嘴转身跑向了里间。
阿芳和东平二人的目光马上就集中在了二娃的脸上,预感这里一定生了什么大事,两个孩子也是想说又不敢说的。
二娃的嘴唇开始不停地在抖动,他在恒昌的背上摸了一把才说:“契柯夫先生来到这里,不到一个月就被人刺死在了街心上。”“啊!”阿芳松开了小儿子。
“后来才听说,这是二个俄国人干的。”东平应了声:“俄国人?”“是的,说是有人亲眼见到的,可这里的巡捕们却砍了一个我们的人头给俄国人看,那个冤鬼又瘦又小”二娃的声音变得沙哑。
坐在一旁的那位老人这时也摇头叹气着,恒昌不知何故也哽噎着说了声:“妈妈,我去帮帮阿姨。”还没等阿芳开口,他已经礼貌的对着东平行了个礼后就跑了进去。
只有八岁大的赵福就不同了,他伸出二个指头比划着说:“听大人们说‘他会造枪’。”阿芳不由得想到了张强。这时的赵福正在问着东平:“叔叔,你会造枪吗?”东平机械的摇了摇头说:“不会。”赵福便仰头靠在了妈妈的身上,脸上挂满了失望。
阿芳用缓解的口吻继续向二娃询问道:“那次带着你的口信去那里的人怎么也没提到过这些?”“那是我忍了好久才瞒下没说的,”他摸了一把失去臂膀的肩头接着又说:“我担心你和大哥知道以后保准会难受,就想着能拖一天就算一天吧,唉,那时方姨也这么说,都怕你们受不了,可是她自己的头在事的第二天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过于激动的东平突然就说道:“我明天就去看看能不能打听到这件事的真正原因。”紧绷的神经让他忽略了叶列维斯基写给他的那些字条已经落在了俄国人的手上。
二娃抹了一把悲戚的脸颊说:“没有用,都快三年了。”
恒昌把刚沏好的一壶茶放在桌子上就说:“阿姨让你们去擦把脸。”他们这才和两个孩子一起去了后院。
走出后门方才见到宽阔的天井,围着它的同样也是除了门窗全都是用石头和泥巴建成,部分墙体还出现不少的裂缝,里面还不时传出零星的声响。方姨把他们让进了左边的柴房,将整好的热毛巾递给阿芳时一语双关的说了句:“没想到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在阿芳没有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时,恒昌却在一旁先开了口:“贺叔叔,我爸爸怎么没和你们一起来呀?”东平稍加停顿了一下就把目光投向了阿芳,与此同时,阿芳的动作也出现了凝固状态,但是她很快就将毛巾丢进了脸盆里蹲下身来对儿子说:“想爸爸了吧,爸爸也很想你们呢,如果不是因为事情太多,他早就要来看你们了。”“嗯,”恒昌点了点头又说:“爸爸要是知道我们不炼铁了,他会生气吗?”“不会的,不会的。”望着她在孩子面前的坚强举动险些让贺东平失去控制,他明白,这是她不想现在让孩子们知道,而这不符常理的表述反而会给其他人带来了恒定猜测,其中就包括已经懂事的恒昌。
二娃见东平也擦洗好了以后,非常不好意思的对二位说:“原先的工厂就在后面,和大哥来的时候一样,没什么变化,就是烧的东西不一样了,要不要过去看看?”
走出后门,方姨就指着紧挨着柴房的木门说:“这是工人们住的。”然后就推开了迎面那扇虚掩着的双扇门,刚才听到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一座十分抢眼的土制高炉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宝葫芦坐落在院落的中央,顶端直接从房顶窜了出去。三名工人踩着木质踏板,转动着圆盘上的泥坯就会在他们的手中变成各则形状不一物体,缸、罐、盆、碗、碟的应有尽有,东边摆放的全都是毛坯,西边都是成品,看一眼便一目了然了主妇的细致。
东平围绕着高炉转了一圈后向二娃问道:“你怎么想起来烧起了这个?”他挠挠头说:“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搞起了这个。”
阿芳接着也问道:“一开始不是说还行吗?”“是那样,几年前我们就买不起矿石了。”“哦?”阿芳似有所悟:‘是的,又多了几张口’她又一次蹲下身来问着恒昌:“你在这里都做些什么呢?”“我嘛,就做些小坯件,大的我搬不动,另外就是在上面勾一些线条或是画上点图案什么的。”阿芳惊叹道:“哟,那可是有本事的人才可以做的呀!”恒昌的脸竟然红了起来说:“都是傅叔叔教我的。”
二娃也有所回暖的赞叹道:“这娃挺有悟性,瞎点一下他都能记住,你还没见过他做的沙模呐,那做的,那填、刮、压的动作比我都熟练。”阿芳在孩子的头顶上摸了一把就说:“真是好样的。”
东平不想谈论这些就指着高炉说:“把它用来烧瓷倒是可以利用的。”二娃乐不可支的称赞道:“你是行家,准能解决这些难题。
正在干活的几名工人知道这位就是恒昌的妈妈之后,没有一个会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瞅了又瞅,翻出的白眼珠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大家重新回到八仙桌前坐下来喝口才泡的茶水时,也不知这水是用什么叶子泡出来的,除有一股青涩味道难以下咽外还伴有一丝微微腥气,不过,现在也不会有谁会提及这些,因为契柯夫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大家的心里比喝它要难受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