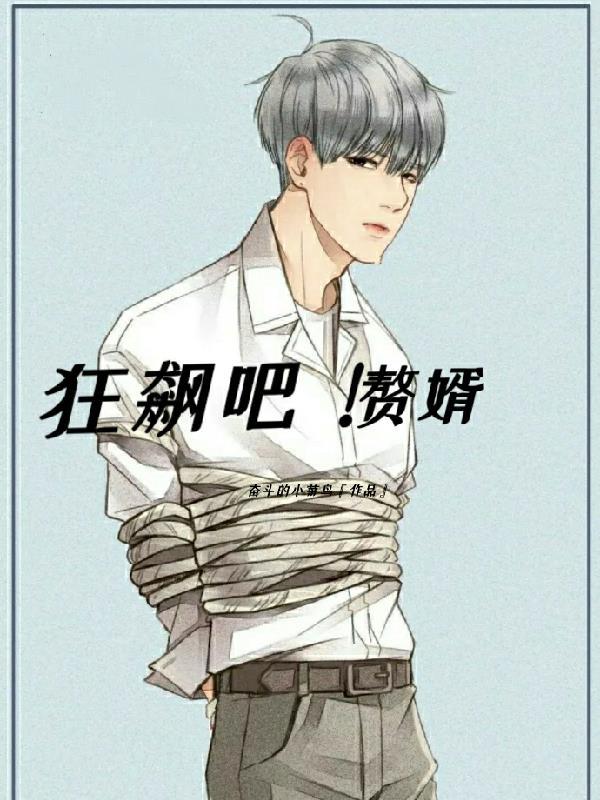笔趣小说>千秋第142章 > 第100章(第1页)
第100章(第1页)
谢萼华忧心道,“为何?王氏虽与我们私交较少,面上却是和煦的。何故做到这个地步,与谢氏宣战?”
谢玄都摇摇头,笑一声,“谢氏?刚刚这位姑娘可得到了他们想知道的,我只是一个身份不明之人,可算不得谢氏。”
谢萼华犹豫道,“可……”
谢玄都知道她要说什么,先摆摆手,向木便将织娘打晕,拖了出去囚禁在房里。
“反叛军将领,名唤沐凤池。”
谢萼华哪里还不懂这其中的关窍,震惊之余只得撑住一旁的浮岚才堪堪稳住自己。
若是这些也就罢了,偏偏与反叛军有勾连,若是王氏将此事透露,无论原先如何,此后必然群起而攻之,谢氏危矣。
若谢玄都承认与谢氏无关,虽可护下谢氏,却是折断羽翼。若不承认,必然血战,生死难测。
“偏偏王氏一群一根筋,自诩卫道者,若是真碰起来,就将有是一场混战了。”
任千忧哈哈一笑,“混战才好呢,水越混,越能摸着大鱼。最好人人相互猜忌,到时候可就不是轻易能过的了。”
谢萼华有些顾虑,“王小姐是为何要提前给你报信呢?”
谢玄都笑了一声,摇摇头没搭话。
任千忧敲了敲桌子,“自是家族与友情难以两全,若是能在事情开始之前,杀了所有事情的源头,不就救下了更多人?杀一人而救万人,想必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所以那封信,是阎王的点卯令。可笑一副却话旧情之表。
谢玄都捏了捏额角,“既如此,巴叶那条运道的分成,全划给王家。”
谢萼华先是一皱眉,后想通了些关键,展眉点头,“是个法子。但是还需能人去运作。”
任千忧笑了笑,“任家,从不缺能人。”
次日,几箱黄金高调地进了王府。虽被王博治赶了出去,却惹人注目。
又一日,便有人在坊间议论,王家半夜开府后门,源源不断地往府里运黄金。众人皆疑之。
其他世家打听后得知,王氏旁系在巴叶河道得暴利,疑似与谢家合作。
众世家纷纷来玄安求见谢玄都,然谢玄都闭门不出,称此事有疑,王氏在巴叶治水挖渠有功,占大头也是有理,且认为女帝是体恤王氏劳苦功高。
众世家闻言,先是打道回府,后于朝大闹,日日扰王氏安宁。无数奏折纷纷上达天听,言及自家劳苦功高,谢氏大义愿出让利益,希望皇室在其他地方补偿。
谢玄都一封奏折交上去,言及自己平了林双外的叛军马匪,受伤在府修养,希望另找能人开凿林双之渠。
帝准许,令何司农派遣。何司农遣调双阳林氏林听风与新官卓越为开河大臣,前往林双。
众世家万分眼红,却只得按下不表。
而后有流言称谢玄都与叛军有旧,谢玄都身份不明,谢玄都开渠是为谋求私利,谢玄都有断袖之癖等。
众人皆奇之,后查出是王氏构陷。众世家皆以为是两家分利不均,王氏不满所做。
虽王氏几番推辞不是自己做的,却仍百口莫辩,众世家皆以退翻王氏以赂谢氏。
而来又大半年矣。
此间任千忧以秉烛公子之名,发《勘世录上册》引得无数仁人志士侧目,学士君子皆以之为奇作,盼下册。甚有山林隐士为之出山,愿做其门客。
玄安谢氏广纳人才,如日中天。
何司农久久伫立在茶楼栏杆处,注视着街道上的万家常态。
嘎吱一声,门扉开合。
何司农转过身来,愣了一下,垂眼含泪拱手道,“任小侯爷。”
任千忧含笑将他扶起来,“何败春,何司农,好久不见。”
何司农也笑了一声,“幸得主君赏识,才能有今日的何司农。当日一观《勘世录》,我便知晓,小侯爷还活着,任氏还有人。”
“升仙城已为死城,永沉湖底,实在是……”
任千忧叹了口气,“若世间有仙,他们也当得了。我实在是不知,我在时,升仙城已然为人迫害,若我当真不在了,又当如何留住他的繁华?守住他们的安宁?”
“我的舅舅,我的老师,我的亲族?他们造了什么冤孽?连死后都被世人污秽扰了他们的清静?永眠湖底,也好过……”
何败春垂眼,落下一滴泪,“哎……如今这世道,也就只有这里还能看见点盛世的样子。陛下很快就会打压谢氏,可,终究是顾此失彼。”
任千忧抬手请他坐下,“我知你难处,若陛下肯看看民生哀艰,便不会拘泥于氏族皇权了。瓦解氏族的,不只有氏族。拆东墙补西墙,终究是徒劳罢了。”
何败春叹了口气,问他,“不知谢相作何打算?”
任千忧晃了晃茶杯,“他的打算不重要,重要的是半年后你的打算。”
说罢碰了碰何败春的茶杯。
“半年为期,若我是你,如今必作壁上观,爱惜羽翼才是关键。”
何败春摩挲了下茶杯的边缘,“半年是河道大体竣工之时,届时世家必然会就此洗盘。何,谨记。”
说罢也回碰了任千忧的茶杯,眺望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又叹气道,“难民更多了,前日我私服出访,才知竟有菜人!断肢残骸,何其可怖!恍然如置地狱哉!愿人间如桃源,如玄安罢。”
任千忧也叹气道,“民生哀艰啊,民生哀艰。我听闻其余世家为防止人口流出,于城门口斩杀离城之人,于城内斩杀无户籍之人。处处皆地狱。”
何败春惨然一笑,“前日,安氏族人送了我一尊木佛,慈眉善目,面相庄然,希望能为其子嗣谋求职位。然佛像其中,竟是人骸!佛之肉身,何故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