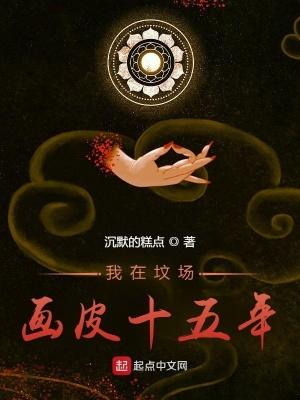笔趣小说>太宗之后再造大唐起点 > 第30章 威震关中上(第2页)
第30章 威震关中上(第2页)
瓦罐不逃井边破,将军难免阵上亡,这些刀口舔血的人,谁又不会担心自己身后事呢?
今天死的是别人,明天谁能保证自己又能苟活?
都说晚唐军士跋扈犯上,殊不知,其实这也怪不到他们头上。自安史之乱后,朝廷信用破产,再让军士们轻易为了空头支票卖命,谁又会信呢?
石壕吏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唐初的时候,府军纪律严明,那是因为人家有土地,有不动产,晚唐军士有吗?就算有,在朝廷到地方,严苛税负捐派下,又能保全多久?
信任这种东西一旦崩塌,就再难建立
而现在,李业所做的,就是要一点点,建立起自己和效节军将士之间的信任。
敬翔退下后,李业方才举杯
朗声道
“我等弟兄今日能相聚于此,同生共死,便是缘分。”
“我李业在此立誓,他日无论何地、何时,只要但有落脚处,就绝不会忘了照顾阵亡弟兄的眷属!”
“在座不少弟兄都是新来的,未必知晓我的规矩,三弟,你来说。”
杨师厚举杯沉声道
“凡军中缴获、捐派、拨所得,须于司马、判官处,一一登记,而后制为公文,传示诸军,不得遗漏!”
“而后逢年节、战胜,以都为例,聚集全都将士,一一公示功勋,当场放赏赐,若有疑虑,可当场质询军司马!军官不得侵吞,事后不得喧闹!”
说到这里,在座之人哪里还没反应过来,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许多在座的新附军官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
此战之后,各军打扫战场,那些新附过来的唐军军官,哪里会像李业那些老部下这么老实?侵吞、私藏缴获,克扣军士赏赐,乃至于因为此事互相争执械斗,都不止一起。
虽然这才是藩镇唐军的常态,但李业决不能容忍!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纪律的口子,决不能开!
他刚才,其实就是在表明,李业自己,无论对将士,对军官,对阵亡伤残士卒,从来都是毫无吝啬,哪怕砸锅卖铁都不会少半分。
但前提是,我可以给,你不能自己拿!这不是李业本人心胸狭隘,这是军队的纪律,没有这样的纪律,之前长安溃败的程、唐两部,眼前刚刚被效节军砍了脑袋的黄揆,都是前车之鉴。
言罢,杨师厚紧接着就念出了好几个名字,俱是新归附不久的队正以上军官。
李业淡淡道
“以上几位,念在初犯,而且本将此前的确尚未申明纪律,不教不株,限明日之内,将侵夺军士的赏赐、抚恤如额还,私藏缴获充公,就当做没生。”
这些老兵油子当然不愿意
有人阴阳怪气道
“军使莫不是喝醉了,可小心营中闹饷兵变啊。”
李业晃动着杯中酒,不屑笑道
“兵变?谁会跟你们兵变?我再问一遍,可服此命?”
无人答话,过了良久才有零星三人上前拱手跪地请罪,其余被点到名字的九人均不言语,态度居傲。
李业对着那三人点头后,让杨师厚代为扶起,随后冷声吩咐
“派人传告全军,此九人克扣所部财帛赏赐,斩!”
随即,帐外早就准备好的二十多名甲士直接冲了进来,新任代替赵密,担任李业亲兵十将的张归霸,亲自动手,带人擒拿九人。
九人正要抵抗,可身边却只有短刃,且刚才宴饮已经让卸了铠甲,而张归霸所领二十多甲士俱是老卒,三下五除二,便一一成擒,推了下去。
一旁看着这一幕的那三个请罪军官,只觉得冷汗淋漓,心中庆幸不已。
座中秦彦皱眉询问身旁的符存审
“符副使,军使就这样宰了这几个人,不怕他们部下作乱?”
符存审不屑笑道
“你忘了?此前收编的时候,就已经全部打散,能有多少亲信?再说,刚才军使说的是什么?‘侵吞所部军士赏赐、抚恤’,这话公示出去,谁会替他们喊冤?”
一旁旁观良久的李振、敬翔二人,见状也是心中思虑良多
敬翔不禁侧身对好友低声叹道
“此子,有王霸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