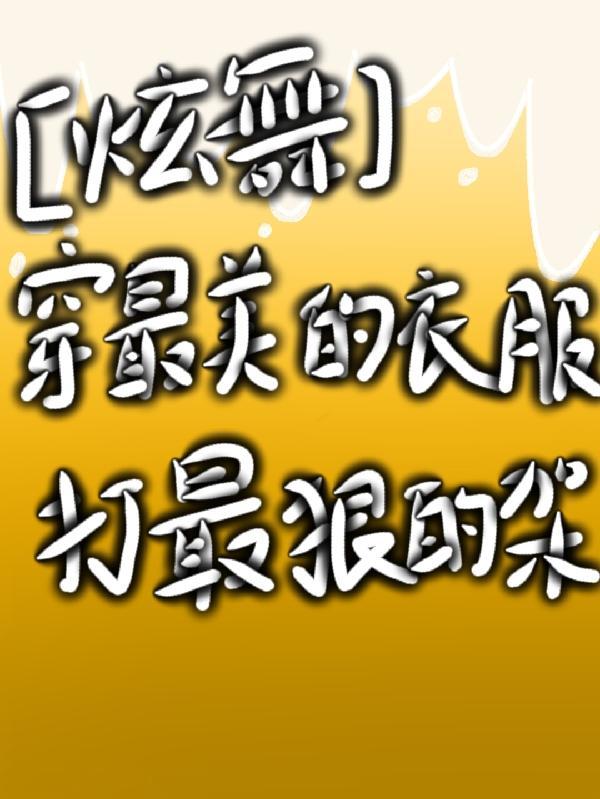笔趣小说>社畜恋爱法则兔美推荐 > 第1頁(第2页)
第1頁(第2页)
壓在她的腰上的手臂,是屬於男人體格的,肌肉緊實,壓的她喘不過氣。
好熱,又不敢動。
貓澤飛鳥瞪著空調,額頭滲出細密的汗珠,像一座大山一般壓在她身上的手臂,如同火爐一般,滾燙的溫度直讓她手心發亮,額頭冒汗。
記憶斷斷續續的在腦中顯現,她小心翼翼的像旁邊瞥,又不敢弄出太大動靜,只看到凌亂的散落在一旁枕頭上的金色髮絲。
但是,這就夠了,已經證實了她的回憶。
簡單點說明,能夠讓混亂的大腦理清現在的狀況那就是,潔身自好了二十多年,連一段戀愛都沒有談過的她,現在直接和一個男人進入到了最後一步。
而且,這個男人,還是昨天還跟她處於正常關係的,連話都沒有多說過幾句,只停留在知道對方名字的階段的普通同事。
如果不是旁邊還躺著一個人,貓澤飛鳥好想咬住被角哭出聲來。
她有罪,她罪孽深重,她睡了正經又禁慾的,在女社員中號稱絕對拿不下的冰山的七海先生。
每天通勤都是西裝筆挺,襯衫沒有任何褶皺,沉穩寡言,不管遇到什麼事情,永遠是處事不驚的表情,仿佛沒有任何的情感波動,人稱大人中的大人的靠譜成年人。
現在,沉穩可靠的七海先生的手臂,就壓在她的身上,且他和她都處於沒穿衣服的狀態。
貓澤飛鳥和七海建人是同事。
說是同事好像也不大準確,七海是企業的正式員工,而貓澤是被社長直接挖過來的,在證券貿易的忙季作為臨時員工,工作一段時間,說是臨時員工,貓澤飛鳥心裡清楚,這份工作其實和派遣員無差。
派遣員是被勞務公司分派的臨時合同工,平時的工作就是什麼都干。
她每天的工作從早排到晚,上到處理文件接待客戶,下到換燈泡修電腦給部長泡咖啡,不過這種事情怎麼樣都好,反正她是按小時計費的,而且薪水高的出奇。
雖然每天比狗還累。
但是看著存摺上的數字不斷增長,這份疲憊又化作了無限動力,不枉費她不遠千里,拋棄狐朋狗友,來到東京。
這一次的合約是九個月,幹完她就會離開,然而這才三個月,她就和企業正式員工睡到一起了。
昨晚,因為簽下了一個大單子,部長一開心就請了手下所有人一塊去喝酒,連帶著她這個臨時員工也一起。
掛著紅燈籠的居酒屋,木質小桌上擺滿了小碟壽司和清酒,迅的喝完一家後又趕往下一場。
直到十二點左右喝的醉醺醺的部長才一抬手,「快趕不上最後一般電車了,你們都快回家吧,明天不要遲到哦。」
既然這樣就不要續攤這麼多次啊,喝的腳下發軟的貓澤飛鳥站起身,套上外套,不忘在心中吐槽。
「等等,貓澤,你家住在哪裡啊,我送你回家吧。」
還沒等她穿好外套,部長從背後拍了拍她的肩膀,掏出手帕一邊擦禿頂的腦袋,一邊笑呵呵的問她,「我開車來的,已經這麼晚了,一個人不安全。」
貓澤飛鳥看到部長無名指上閃閃發光的婚戒,心中早就把部長罵了一千遍,作為成熟的打工人,她只是擠出微笑,委婉的表示拒絕,「有人和我一道,您回去晚了夫人會擔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