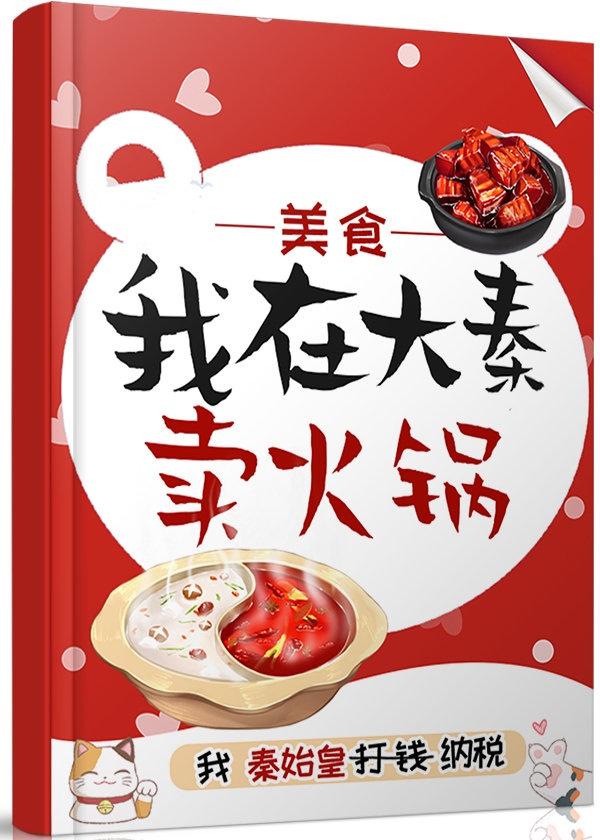笔趣小说>太子妃只想摆地 > 第83章(第1页)
第83章(第1页)
台下有人看不过眼,喊道:“这不是欺负人吗?江小姐都没拿兵器!”
还有人附和道:“就是!刀剑无眼,万一伤着人了怎么办!”
在一片嘘声带来的压力下,时异只好把刀扔去一旁。可是如此一来,气势上就显得矮人三分,失了先机,最后果然草草落败。
江御暮很有主人翁的风度,弯腰捡起时异的弯刀双手递上,对他温柔一笑。
可是等到时异低着头走下擂台,她盯着他逐渐隐入人群的背影,眼中的笑意却已尽数散去。
他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江御暮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穆归礼那夜,二人曾交过手。她当时手执长剑,一出招便带着杀意,相当于逼穆归礼全力应对,从而探知他的实力水准。
结论也很明确,穆归礼的身手远逊于江御暮,她若不放点水,他怕是连十个回合都抗不过去。
时异则比他强出许多,即便经了一遭中毒又解毒的折磨,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却也能与江御暮力战几合,抗下她二十余招。
问题就出在这里。
江御暮记得清清楚楚,荒院谈判那日,穆归礼为了强迫时异服下毒药,曾与他打了一场,而且赢得无比顺利,时异甚至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这难道还不可疑吗?
若换个奴性重些的人,不敢为了保命奋起反抗,跟主子交锋时束手束脚也就罢了。可从时异那日的表现来看,他并不是这样的孬种。
也就是说,时异明明有实力战胜穆归礼,也有胆识反抗他的无理命令,更有保命求生的本能欲望,可是不知为何,他还是败了。
败得干脆,败得利落,败得不合常理。
想到这里,一个念头忽然跃入江御暮的脑海——他当真与穆归礼反目成仇了吗?
会不会从一开始,他就是穆归礼埋在她身边的一颗暗棋呢?
江御暮居住的偏院少有人至,如果穆归礼想与时异交谈,只需挑个她不在府中的时间翻墙前来即可,左右这也是他做惯了的事。
不过自打进了江府,时异就一直被锁在偏房里,探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正经算起来,今日还是时异第一次出门“放风”呢。
他虽见过费红英,却连她姓甚名谁都一无所知,即便刚才在擂台上打了个照面,他也没认出眼前这位国师就是所谓的“神医姑娘”。
说起来,时异对江御暮的了解也不算多。因她早有防备,所以让他参与计划时没交实底,只说她不愿草草选人成婚,故而找几个“自己人”相互配合,唱一出双簧。
如果时异仍然效忠于穆归礼,那么他向她“投诚”的举动就很值得玩味了。
早不投诚,晚不投诚,偏偏在费红英让穆归礼暗中提防江家之后才投诚,这个时机选得也颇有意思。
她倒要等着看看,穆归礼打算怎么走这步棋。
随着一声锣响,费红英再度开口:“第二场,江小姐胜!下一位,姜敬,姜公子何在?”
江连镜动作极快,此时已换上一张新脸,笑眼弯弯,观之可亲。
自报家门后,江连镜冷不防提出了一个古怪的要求,使围观众人都为之惊诧。
“江小姐,总是那般打打杀杀的有何趣味?想不想换个新奇的花样?”
先前约定好的流程中并没有这一环,江御暮短暂思考片刻,决定顺着他的话发问:“什么花样?”
江连镜伸出一只手:“掰手腕,如何?三局两胜。”
此话一出,台下诸人又叫喊着插起话来。
“你这厮好生刁滑,掰手腕算什么新奇的花样,不就是想趁机占人家姑娘便宜吗?”
江连镜上前一步,从袖中掏出一方绸帕,嬉皮笑脸道:“兄台这可就误会了!在下为了避嫌,还特意准备了一块帕子呢。隔着如此厚实的帕子掰手腕,也算得上君子了吧?”
这样无耻的言论,自然又引来台下一大片议论之声。
石涅气不过,直接扒着茶馆二楼的栏杆向下喊道:“哪来这许多借口?我看你是自知打不过江小姐,才出此偏门怪招,想靠一把子傻力气取胜吧!”
话音一落,台下就响起阵阵附和声。
“这位小兄弟说得在理!”
“就是就是,比武招亲比的是武功,又不是力气!”
“姓姜的,你就算这么赢了,可也不能服众啊!”
面对众人的指责,江连镜佯装讪讪,用衣袖擦起汗来。
江御暮适时出面解围:“没关系,就算是单比力气,我也有自信不会输给他。”
众人这才止了骂声,可是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好像一片好心都被当成了驴肝肺。明明方才还站在江御暮那边,现在却反过来有点希望她吃瘪了。
江御暮不甚在意,向江连镜伸出手道:“开始吧。”
江连镜却摇摇头开始挑剔:“不不不,现在开始还太仓促了。既然要掰手腕,咱们便要坐得稳稳当当的,把胳膊肘抵在桌子上,那样才好发力呀!”
江御暮微微皱眉,正要开口质疑,江连镜却避着众人的视线给她使了个眼色。
她很快反应过来:“也罢,那就借张桌子来吧。”
江连镜从荷包里掏出一块碎银,向台下喊道:“不白借啊!”
银子的力量着实不小,擂台斜对面一家餐馆的掌柜直接命人将一张方桌抬上擂台,还搭了两把木椅,一起摆放整齐。
江御暮和江连镜面对面坐下,用绸帕垫在两手之间,像模像样地掰起手腕来。
因着距离拉得足够近,此刻他们终于可以低声交流,不必担心被台下人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