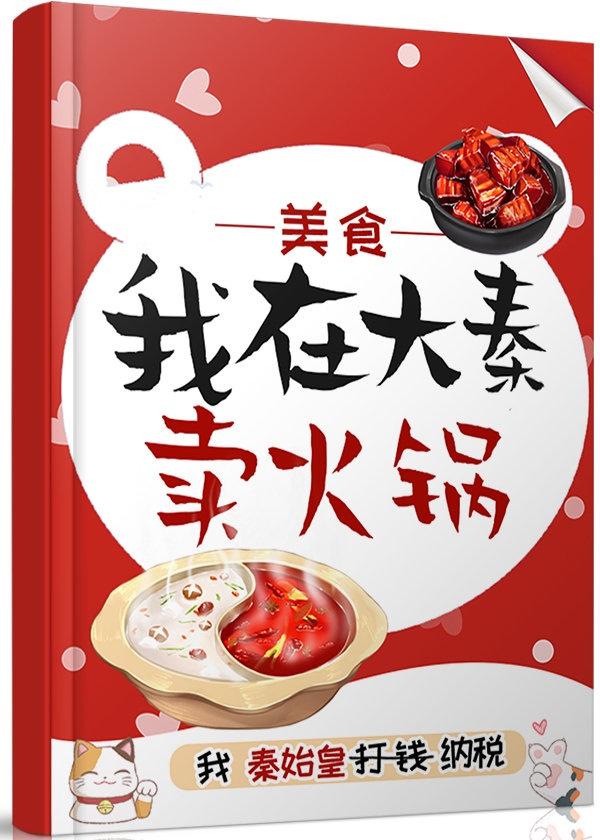笔趣小说>反派兼职万人迷[穿书 > 第107章(第1页)
第107章(第1页)
不等山姆开口,他又补充了一句,“是什么吓得你在得知真相后放弃了如日中天的苏富比。”
虽然胃里没有什么东西,可在这种氛围下唐烛实在很难有胃口。他本想劝说付涼说话至少要顾及到他们此刻还在人家地盘上,还没来得及插嘴就又听见蟾蜍——不,是老山姆的声音。
“你从哪里听说这些的?”老头的声线平缓可音量却放大了,“空屋?还是公爵那里?等等,既然你能出现在伦敦,并且试图旧事重提,定然是得到了公爵的默许。”
“公爵的想法我就不清楚。”付涼淡淡说,“但知道你的就够了。”
老山姆咯咯笑起来,最开始这笑声还算是有所顾忌,后来便放肆起来,直到因为大笑某些口水流进了他的气管使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女佣为他端水又拍背,几分钟以后山姆才筋疲力尽地瘫在座椅上问:“咳咳…殿下知道每场拍卖,我们为什么会让甚至拿不出起叫价的市民入场吗?”
他继续自问自答:“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当日能得到竞品的人在哪几个人之间产生。竞品主人的身份是注定的,这个事实并不会因为谁在围观而改变。”
“我了解你的艾伯特,十年前你就能拍下竞品,可你没有那么做。十年时间,迫使你远离这场竞拍的原因只会更加根深蒂固,你拥有这份能力,但你早就选择了不入场不是吗?”接着,老男人抬起肥胖的手指挪到舞台的方向,又说:“来吧,我的孩子们在德意志找到了一本好书,待会就会有人来表演,我猜你一定会喜欢。与其用你回来解开十年前的谜团这个理由来诓我,不如坐下来好好享受。”
听完这些话,唐烛却现身边的青年没有反驳。
与付涼平素的脾气大相径庭,他只是面不改色地用餐具切着一份牛排。在他专心致志完成切割工作时,老山姆所说的表演者也穿着老式服装登上了舞台。
与唐烛抱有同一种心情的人还有对面那位本该看歌剧的老蟾蜍。
实际上,老山姆终于觉今日的付涼有什么地方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他开始后悔先前说出那些用作类比的话。
餐厅内上演了一场因表演的存在而过分典雅的拉锯战。
双方僵持不下。
最先开口的人只能是唐烛,“山姆先生,我们今天来拜访,的确是……”
“等等先生,我并不觉你可以对皇室的——”可老山姆并不觉得他的言能起到任何作用。
“他可以。”
付涼的声音不算大,声线却压地很低。
“在伦敦活了六十年,没人教会你打断别人是不礼貌的吗。”
唐烛讪讪地转脸看向错愕的老山姆,又即刻回过神去拉付涼的衣襟。
啧,怪不得要提前说让他帮忙劝着点儿。
对方只是把切好的牛排放在他面前,然后拎起餐刀用红酒杯内的白色丝绸擦起了刀面。
“说了那么多废话,你无非就是觉得十年前我没有选择追查的真相,就算你今天说出线索,我也没可能查到最后。而这样做,只会增加皇室对你的敌意。可你真不想知道,十年前那场抢劫案的真相是什么吗?”
“不……十年、十年前只是一场意外!”老人激动起来,试图从椅子上站起来却只是咳嗽地更厉害,“咳咳咳!艾伯特…你不要想着欺骗我!我们所说的事情完全没有关联!一切都只是意外!”
“只是意外吗?”
付涼垂眸看着手中光洁如初的餐刀,平静道:“十年前,有人把伯爵夫人的桂冠带出山庄,几经辗转去到了黑市。在那里,某个年轻的商人开出了一个让佣人无法拒绝的价格。
那人就是你唯一的儿子,他试图得到那顶自己在拍卖会与展览会见到过无数次的桂冠,可惜他注定不是竞品的主人不是吗?
十一月初,皇室放出伯爵夫人染病去世的消息。他以为自己终于拥有了它,可还没等到圣诞节……”
“别说了!”老山姆几乎要从椅子上摔下来,他的额头全都是汗,可付涼并没有打算听从他的意见,继续讲述道。
“他就被杀了。在他保险箱里,只留下一顶桂冠。五年后,当你终于释怀,也逐渐说服自己相信当年小儿子就是被盗贼杀害的。
可就在你准备在拍卖行上展示消失已久的桂冠时,却现自己也被盯上了。你手足无措,只能装病,四处躲藏并且写信给空屋寻求一个活下来的办法,而给你回信的人,就是我。”
青年将餐刀随手丢上桌面,“我帮你策划了一场百万富翁藏品被洗劫并在角逐中失去一只眼睛的戏码,使得桂冠流入俄国黑市,而你也保住了一条命。”
老山姆跟着抬起手抚上了自己的义眼,显然这个事实让他难以接受。“不、不是的!当时!我知道只有公爵大人能救我…然后我写信给他,让他看在卡尔特的份儿上帮帮我!他答应我只要我不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他就会找人为我求得一线生机!我记得、我记得当时的回信并没有注名,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