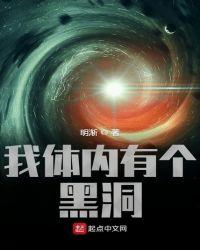笔趣小说>欢迎回家的英语 > 第22节(第1页)
第22节(第1页)
时为说:“你需要多少种?”
丛欣说:“七天,不同的菜单,可以吗?”
时为握着车把望天,重复她的话:“七天,不同,的菜单?”
丛欣看看他,问:“能做吗?”
时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说:“你要我做当然是可以做的,但是我算过全日制厨房培训和研发的预算,虽然半年了基本没动过这两笔钱,但原本就比中餐和西餐厅都要低不少……”
总之一句话,又是一个“得加钱”。丛欣单手脱把,抓了抓头发。
时为笑出来。
直到她又转头看他,他才不笑了,说:“你别挠头了,不就是七天不同的半自助菜单嘛,我给你想办法。”
第27章五百英里
时为回到职工楼的那个夏天,朱明常教他做菜的时候,经常对他说起自己刚入行时的事。
那是1955年,当时的朱明常也是十六岁,在后厨做杂工,也就是后来粤菜流行起来人们常说的打荷。
不管叫什么名字,杂工或者打荷,拿的都是厨房里最低的工资,干的是最苦、最累也最脏的活,每天最早上班,夜里最晚下班,磨刀,洗锅,备料,擦洗灶台,打扫卫生,这些准备和收尾的活儿都由杂工来做。
但杂工虽然辛苦,却也是最有机会学到技术的岗位,每天从一早干到深夜,给后厨的老师傅打下手,只要人足够勤力,足够有眼力见儿,做上一阵,厨房里怎么回事就能摸清楚。
而中餐厨师一般都是师徒制的,做师父的总有几样独门秘技,不可随意外传。于是便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雇杂工绝对不用年纪大些的熟手,怕养不熟捂不热,也怕是同行来偷师。
所以这个岗位上都是刚入行的小孩,十几岁的年纪,什么都不会,甚至有些木头木脑,就像当年的朱明常。
而当年的师父还是民国时候留下来的老人。江亚饭店虽然已经变成国营单位,后厨的老厨师们总还保有着些过去的习气,讲究的也还是过去的规矩。
徒弟们送烟送酒自不必说,休息天还得上师父家里干活儿。做师父的有时更会使出些手段,比如故意让徒弟徒手拿起很烫的锅子,然后叫住徒弟,慢慢告诉他,在厨房这个地方,哪怕再烫的东西只要拿上了,就是不能随便撒手的。这一关,说是教训也罢,搓磨也罢,考验也罢,当时很多人都经过,只有让师父满意,才会传给真技术。
十几岁的小孩大概都有些中二病,时为听完甚至有些跃跃欲试,以为朱明常也会给他来这么个考验,然后他意志坚韧,天赋异禀,神功护体,完美通过考验,得到朱师傅传授的独门秘笈,自此成为一代厨神……
只可惜,这一切只存在于他的想象当中。
现实里,朱明常一边洗菜切菜,一边接着对他说:“那是真的会烫伤的,当年就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学徒,因为这个把手伤了,最后调去了别的岗位工作。这也就是在国营单位,徒弟算工伤,有劳保,老师傅还吃了批评,要真是民国的时候,这个人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我那时候就记住了,心里想,无论是眼下做徒弟,还是以后有机会做师父,不能伤着自己,也不能伤着别人。”
时为听了,觉得是在点他开车离家出走那回事。几个月前,警察也对他说过,万一出点事,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后果不堪设想。很严厉的用词和语气,但他当时没怎么听进去。
朱明常却一句没提,切了葱姜,起了油锅,继续说厨房里那些事的:“其实,过去那些老师傅总怕被别人偷师,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就那几招,几十年不变,也没多少技术含量,给明眼人一看就透。
“要是一个人摆个小摊,那还能说光靠手艺。但凡是上点规模的厨房,技术最多只能占三成,管理占七成。有些东西你不如大大方方教给徒弟,年轻人虽苦虽累,但在你这儿有机会学到技术,才会觉得有盼头,愿意继续给你干下去。
“而且,哪怕是老师傅也不能不学习。就像前两年我们单位改制,一批批的下岗,最后能留下的还得是学历最高的厨师。人家当兵复员回来,二十多岁才进厨房工作,哪怕再累也把在职大专读下来了,会做量化,懂管理,在他手底下出餐无论品质还是速度都是有数的,其他人不服不行……”
时为听着,又觉得是在点他。同样是要他回去读书的说辞,但不知道为什么,这番话他能听进去。
也就是这样,在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主动说愿意重新开始上学,但同时也提了要求,想继续住在职工楼,并且转到丛欣读书的那所高中。
时益恒起初不同意,还是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里去。那边学习进度抓得很紧,他休学半年多,已经耽误了。
最后还是朱岩又从拉萨回来了一趟,想办法把他转学的手续办妥了。
她找了那所区重的校长,她过去的老师。那里其实也是她的母校。老师当年很以她为骄傲,现在更是这样,带着她到处转了转,看改建之后的校园,还去校史室看了当年毕业拍的集体照。
透过仿佛被时光模糊的一扇玻璃,她在那张照片上找到小小的一个自己,没有笑,显得格外白而安静,与周围人格格不入。当时,她也是十六岁的年纪。那一刻,朱岩感觉到一种命运弄人般的神奇,自己努力想要离开的地方,似乎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
借读手续办的太晚,交完费用,签了协议,已经是开学两个月之后了。
那是2008年11月,时为开始在那里读书。
学校建校很早,但没什么名气。因为在市中心老城厢的人口流出区,校舍很小,学生也少,有些上年纪的老师还是一口上海话,体育课看着学生在操场上跑圈,嫌他们拖拖拉拉,就会拿个电喇叭喊:拿了了踏咸菜啊?!周围居民都能听到。
可以说跟他从前读的那所私立截然不同,但就是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不知道为什么,反倒让他觉得自在了。
而且,他还跟丛欣成了同桌。
或者严格地说,也不算是真正的同桌。为避免互相影响,学校实行一人一桌,两边隔着窄窄一条走廊,可以说没有同桌,但左右离得都不远,也可以说两边都是同桌。
丛欣就坐在他右手边,仅仅一臂的距离。
学校离家不远,也没有住宿。每天早上,他们两个人都是骑车上学。时为从职工楼出发,丛欣从新家过来,骑到距离学校几百米的一个路口汇合。大多是时为早到,在路边单腿撑着车等她一会儿,她到了,再一起往学校去。
放学也是两个人一起走。学校多少年保持最佛高中的称号,高考成绩基本靠天分。高二照样四点半放学,周五更早,更没什么晚自习。他们一起回职工楼,一起写会儿作业,然后一起吃晚饭。
沈宝云为此感谢张茂燕,认为是丛欣在帮助时为学习。
张茂燕也为此感谢师父,让家里这张刁嘴有了个吃口好饭的地方。
凭良心说,长大一点的丛欣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挑食了。在江亚饭店职工食堂吃了几年,后来哪怕学校的食堂饭她也能吃下去,但那只是为了活。但凡有选择,她照样挑的不行,米饭一定得干干净净,不能沾上任何汁水,蛋羹必须完美镜面,蒸鱼要一点腥味都没有,但又不能让她闻到丁点黄酒味道,黄鳝只吃划成丝的,不吃切成段的,牛肉得有煮到软糯的牛筋,但也不能让她觉得肥。
人大了轻易饿不死,张茂燕不再惯她这毛病,当然关键还是厨艺不行,想惯也惯不了,她自己也在职工食堂吃了几十年,回到家里会做的无非就是那几个最简单的菜。
丛欣背后吐槽,说她家天天番茄烧蛋、紫菜汤、洋山芋炒鸡毛菜,妈妈烧的大排骨咬起来像泡了酱油的棉花胎,还是外公做的好吃,外公对她最好。
听得朱明常笑出来,还非得绷着脸,说:“你写你作业去,我叫吃饭了再出来。”
时为旁观,在心里哼哼,马屁精,矫情鬼。但有时候他自己去给朱师傅打下手,切肉的时候还是会给她修到她要的那个完美程度。
丛欣偶尔也会凑过来帮忙,或者说帮倒忙。
比如最简单的打蛋。她把蛋敲开,要是发现系带长得明显一点,或者蛋黄颜色红了些,就会觉得不对劲,迟迟疑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