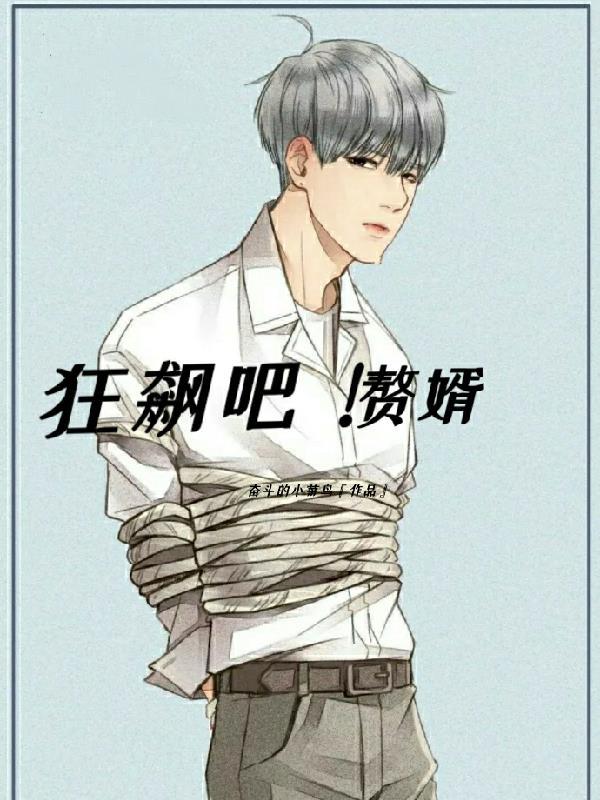笔趣小说>弃奴持刀重生 今州 > 第57章(第1页)
第57章(第1页)
人各有职,专项一职就够了,他最要做的不是干涉朝政。朝堂的那些事需要执政者站在太阳底下,光明正大地接受世人的审视和监视,而谢漆这么久以来干的是监视别人的活儿。他习惯了在暗处。
谢红泪将在十月二十这天晚上秘密进宫来,高骊说什么也要谢漆在场,这个他倒是欣然应允。
前世暴君陛下的红颜知己啊。
逢风雨夜,及风雪夜,谢漆便常在东宫得到讯息,道脾气火爆的暴君陛下又在宫外来的花魁娘子膝上醉卧。
上次烛梦楼初见她演奏箜篌,高骊并没有什么感觉,只不知此番将如何。
谢漆仔仔细细地查过谢红泪的来历,查到她六岁便被送进烛梦楼,身世难寻,年少时不止一次寻死,后来大抵是认了命,不再到处折腾了。十二岁时挂牌,先从清倌人做起,精通数种乐器,歌舞俱佳,又兼生得一张倾城脸,身价越涨越高。十六岁时撤下清倌的牌子,一夜被各浪荡子哄拍出万两黄金,身价飙升成烛梦楼当之无愧的花魁娘子,此后更被冠以“黄金娼妓”的外号。
迄今为止,她在那销金窟里待了二十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若心存某种绝志,二十年里能经营的事情并不少。
她在十九岁那年收了一个养弟,取名为谢青川,背地里不遗余力地培养。谢漆记得前世
第1回春考放榜,谢青川只在许开仁之下,后者一直为吴攸办事,谢青川是入大理寺投靠梁家。
最后一年他在高沅那儿时,也曾见过谢青川几回,端的是芝兰玉树,虽从风尘之地来,却不见靡艳钻营,更看不到自惭自轻,让人好感倍加。
谢漆整理着思绪等夜幕降临,上午高骊上朝,下午在御书房,白天暂时不需要他,趁着换班的空档,他走了一趟慈寿宫。
上次梁太妃的眼神让人难以忘却,更遑论方贝贝前几天嗷嗷呜呜了一趟。
他手里也有一份记录了梁太妃一生当中的重要经历。世家贵女,牡丹般的花颜玉身,少女时也曾打马过长洛的繁华大道,惊惹多少秋风花架。梁奇烽只有这一个嫡亲妹,梁家对她的期望不可谓不浓厚,但当年的梁小姐最初的议婚之人不是后来的幽帝,而是旁的儿郎。这段杂谈如今只找得到梁太妃的只言片语,找不到曾经与她订过婚约的那人情报。
幽帝早年最宠爱梁妃,说是爱之如狂并不为过,为此故意将那前婚者的事迹抹除也不足为奇。
虽然记录上没有明言,但排除不了,她在宫中的三十年并非心甘情愿的可能性。
谢漆来到慈寿宫拜见时,梁太妃的贴身嬷嬷都是惊喜的,带着喜出望外的神色一路轻快地引他到正殿里去:“娘娘,谢侍卫来看您了!”
梁太妃正坐在之前与之对弈的椅子上,好似自那天下完棋之后,她便一直在这里下到今日。
看到谢漆的第一眼,梁太妃眼里又浮现了些如遇故人恍如隔世的飘渺感,回神后才让他不必行礼。
谢漆再次坐在醉金棋盘的对面,梁太妃笑意盈盈地端详他,开口的熟稔语气仿佛他们是忘年交,又好似他们是故人:“谢漆,你近来如何?”
“托太妃娘娘关怀,卑职近来甚好。今日秋光溶溶,陛下想起太妃娘娘宫中孤独,特令卑职得闲前来陪伴娘娘闲话。”谢漆恭恭敬敬地行礼,搬了高骊当借口,垂眼不直视,又恭顺地问了她的近况。
“一成不变罢了,日子毫无新鲜之意,见你们年轻人前来,方能觉出自己还有几分活力。”梁太妃微笑着催促他一起下棋。
谢漆陪她下棋,客客气气地闲话几番,委婉地把高沅的事说了。
“卑职上回来太妃娘娘宫中请安,回去的途中遇见了九王爷,此后便听闻九王爷感了风寒,身体抱恙。”
“是么?”梁太妃停顿了片刻,轻叹道:“那孩子,身体还是这么弱。大约是因为换季了,他最是容易受这天气摧残。”
语气中透露着的是浓浓的怜惜。
“九王爷大约是惦念着太妃娘娘,来往时受了寒气。”谢漆听不出什么奇怪的,忍着牙酸说出这话来,“母亲不在身边,身体便自然而然地疏忽了。”
梁太妃清细的声音里涌出了哀愁:“他有今日之病体,也全赖本宫底子不好。”
谢漆静静地听她细细诉说。高沅今年也才十五,而她入宫三十年,在高沅之前怀过四次身孕,皆因各种原因小产,身子骨越的娇弱。高沅出生时甚至差一点因难产而母子双双病亡。
或许是因为过去太久了,现在梁太妃把旧事说出来时,语气中尽是一种风轻云淡的漠然。仿佛痛若剜骨的不是梁氏,而是某个素不相识的街边人。
谢漆听到她轻描淡写地说着自己卧床三月伤口仍然复裂的时候,心中一阵惊心动魄,忍不住抬起眼去端详她。
大抵是他不过才见了这位太妃几次,还不了解她,初见时对梁太妃怯弱、不像世家贵女而像小家碧玉的印象被冲散掉了。只有孤独寂寥依旧。
察觉到谢漆的视线,梁太妃不好意思地朝他微笑:“本宫一上年纪便越像个老顽童了,口无遮拦地和你说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当真失态。来,我们继续下棋吧。”
谢漆心中复杂透顶,扫过这正殿里那些侍立的呆若木头的宫人们,那稍微机灵些的嬷嬷忙着去料理一宫的内务,而其他的年轻太妃们不是疯疯癫癫,就是哑巴一样的沉闷。至于她的亲生骨肉,却在病榻上狂地让自己的侍从来杀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