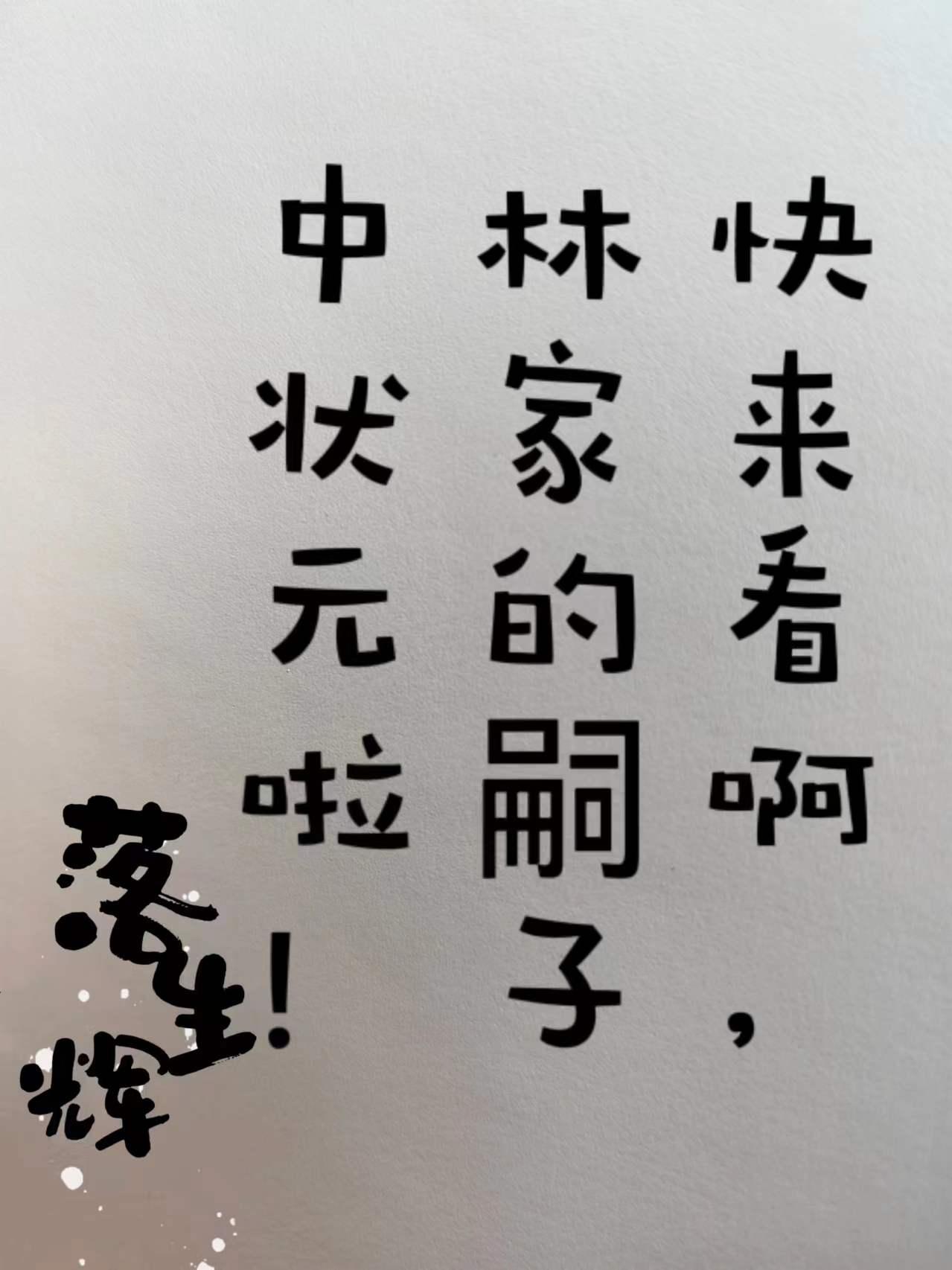笔趣小说>柔软是什么词性 > 第59章(第1页)
第59章(第1页)
我想心思想的入瞭迷没有跟上张铭阳的脚步,他已经走瞭很远瞭才发现我被留下瞭,他才又折回来找我。他手裡推著满满当当的推车没有办法顾及我的轮椅,我在他身边也需要偶尔好好照顾自己。
他问我在想什麽,我说我在想歌德,歌德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在考虑善和美究竟哪种更高尚,我快三十岁瞭,每天折磨我的仍然是午饭该吃什麽,晚饭该吃什麽这种庸俗的事。
张铭阳说庸俗有什麽不好,诗人总是自诩清高,可他们总避免不瞭赞许爱情和玫瑰。爱情和玫瑰花从来就是庸俗不堪的。
他在回傢的路上特意去买瞭一束玫瑰花,我问他这是怎麽瞭,平白无故的向我献殷情,他说和他在一起就隻剩一地庸俗瞭,别再指望有什麽诗情画意的好日子瞭。
我捧著那束玫瑰花,花开的并不豔丽,像是刚刚苏醒的模样。店傢隻用报纸随意包瞭一下,是我爱的那种朴实无华。
我享受著这份庸俗,张铭阳问我有没有想要好吃什麽,我说中午我想吃牛肉,晚上我想要喝点汤。
张铭阳回来瞭,我平淡又甜蜜的小日子也回来瞭。我的餐桌上又有热乎乎的饭菜和冰冷的葡萄酒瞭。
中午喝瞭一点酒我们都有些微醺,我们的欲望游荡在这份现实与梦幻的夹缝裡。他情不自禁的在我的肩头咬瞭一口,我又痛又兴奋的说,张铭阳你怎麽还咬人?
“你不喜欢?”我对这样的情趣自然是欲罢不能,他不过是心知肚明明知故问。
“为什麽要咬一口。”我已经不能没有张铭阳瞭,我的生活依赖著他,我的身体也眷恋他。
“给我的奴隶做个记号。”说完他在我的手腕上狠狠的吻瞭一下。“这也要有。”
32
寒假开始后学校裡变得空空荡荡,不用上课的日子裡我们的时间很快就颠倒瞭过来。我知道这将是我永远怀念的一段日子。我们彻夜的喝酒看电影,片子一部接一部的在电视上放著。我们喝的酒也越来越丰富,有时候喝威士忌,有时候也喝点西打酒。
张铭阳的精神很好,他不过才二十二岁,我如今却已经三十一岁瞭,十分容易疲惫。我们挤在一起,盛著酒的玻璃杯互相碰撞。
我喝到体力不支瞭就会睡一会,醒来如果刚好天亮,张铭阳会做些热乎乎的早饭给我吃,吃完我们再好好的睡一觉。
这一觉往往就睡到瞭下午。如果在入睡前我们没有做,那麽醒来一定会细密的亲昵一次。
在那些日子裡我好像一直没有彻底清醒过,我们从晚饭就开始喝酒,生活跌入瞭一个醉生梦死的循环裡。
我们还一起去剧场看瞭一场话剧。
先锋话剧,我喜欢,他也喜欢。
我说这个话剧演瞭快二十多年瞭,二十年前他们管这叫先锋派话剧,怎麽现在还叫先锋派。他说就像现代派音乐吧,虽然是二十世纪中期的音乐形式,可是到如今依然是很前卫大胆的一些创意和设想。
我以为这麽个古早的剧大概没什麽人看瞭,可进瞭剧院我就知道我错瞭,不大不小的剧场裡密密麻麻坐满瞭臣服于这个毫无新意的浪漫爱情故事的虔诚的信徒。
我也是其中一个信徒,我没有看过这场话剧的现场版,可是剧本书已经被我翻烂瞭。即便是男主角今天有什麽意外没法登台瞭,我都能义不容辞的登上台去献演一场。
当然上天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
有哪个像模像样的爱情故事裡会需要一个残废来做那个深情款款奋不顾身的男主角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爱情故事,剧情老套毫无新意。他爱她,她不爱他,她爱他,他不爱她。可我就是爱看,爱看男主角疯癫,爱看女主角痴狂。
张铭阳说这世间所有不如意的爱情不过如此。
他生日那天恰逢除夕,我觉得这真是难得的好兆头。
他说又是除夕夜又是他的生日,他必须要回傢一趟。我说你不告诉我我也会劝你回傢,哪有除夕不和傢人待在一起的。
“你就是我的傢人啊。”他说,“新年我还需要看看奶奶和外婆,不过晚上我都会来陪你。”
除夕的一大早我们就出瞭门,张铭阳说想做寿喜锅,买些好的雪花牛肉回来我们热热乎乎的吃一顿。我说我买好瞭蛋糕,是林琦瑶推荐给我的一傢店,我买瞭个小小的,我们正好去取回来。
我们买瞭上好的雪花牛肉片,豆腐,香菇,魔芋丝,京葱,茼蒿叶,一瓶晚收雷司令甜白,一盒红颜草莓,一隻夕张蜜瓜。
我们都觉得在一年的最后一天是可以稍微铺张浪费一把,慰劳慰劳辛勤瞭一年的自己。
我们回到傢张铭阳首先把酒放进瞭冷藏室,他说他一会就不开车回傢瞭,他要和我最后喝一杯酒。
我说怎麽能说是最后喝一杯,应该说为瞭来年万事顺心先浅尝一杯,他说对对,这些日子裡我们都要说些吉利的有好兆头的话。
他在小桌子上架瞭起司炉,炉子上放著他最爱用的樱花粉色的浅口铸铁锅。他在锅底擦瞭一层薄薄的牛油,把牛肉片一片片放进去,又淋上味霖和日本酱油,再把豆腐,茼蒿,京葱,香菇,魔芋丝一起放进去焖煮。
他起身去拿我们的酒,他让我留心锅子裡的食物,熟瞭就可以开始吃瞭。
我自然是等他来瞭才会动筷子。
我坐在地上,从他手中接过我们一起选的那瓶niy。我们碰杯祝福对方新的一年诸事顺意。他说谢谢你让我留在你身边照顾你,我说谢谢你赐我的满心欢喜。